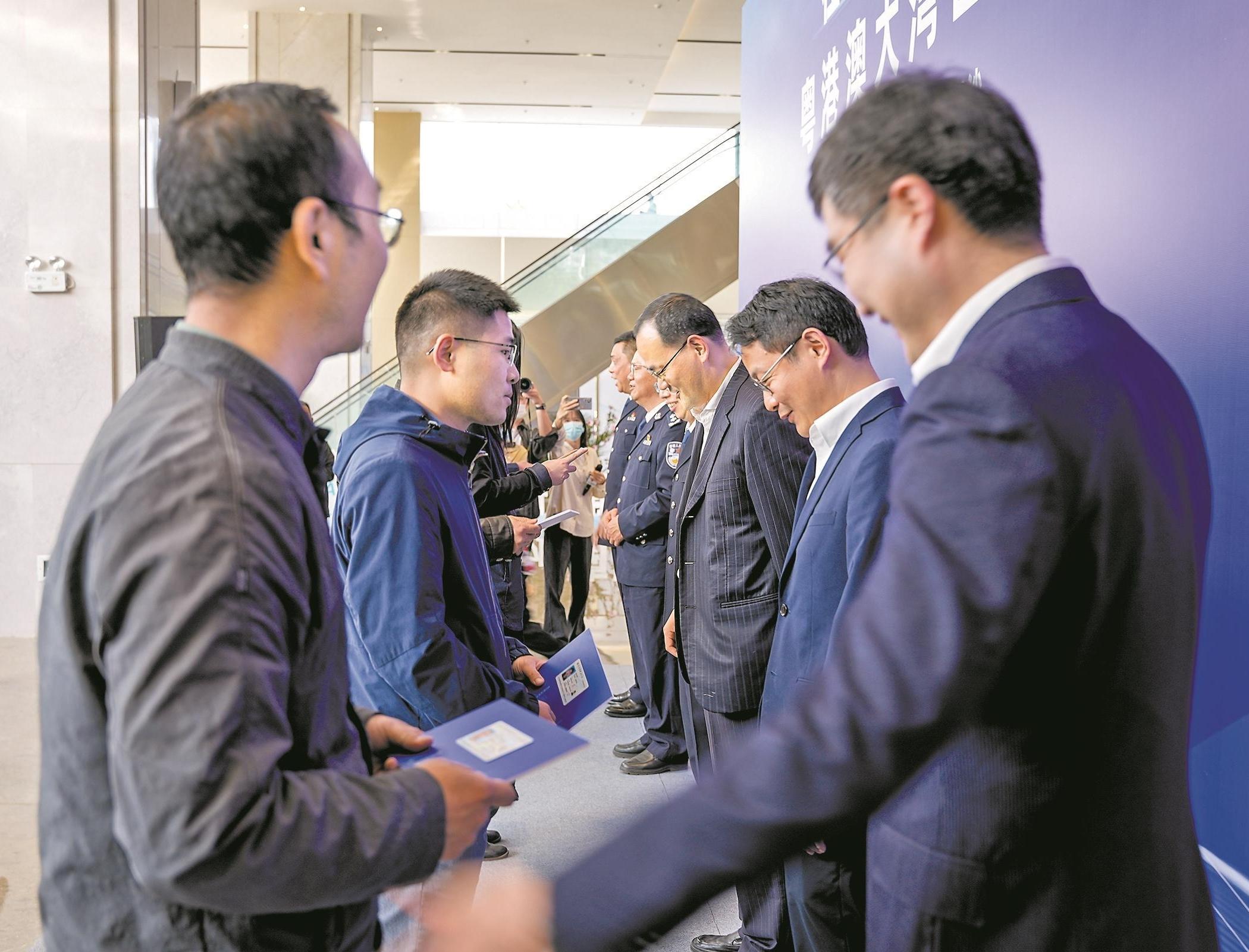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花地 | 邢小群:难忘赵树理


文/邢小群
1965年年初,我随父母从湖南长沙来到山西太原。当时,父亲在湖南,感到气候不适应,向上级打报告,希望调到河北工作。
冀中一带是我母亲的家乡,也是战争年代父母所在部队活动的地方。1958年,父亲曾经下放到河北省文联,在保定办公。他也曾以作家身份下放到石家庄国棉一厂。
上级回复,河北文联的干部下乡四清去了,一时联系不上,问我父亲愿意不愿意到山西省文联?父亲一想,山西的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几位作家他都认识。孙谦还是他在电影局时的同事,就同意到太原。
住了几天招待所后,我们一家大小被带进一间像庙堂一样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告知这是我们的新家,并征求父母意见,如何简单装修一下。记得当时,我们眼中充满好奇,心里却感到从里往外的凉——这房子能住人吗?抬头可见年深日久的梁、檩、橼之类的木建,屋内没有暖气。
据说,山西省文联对我们家的到来,没有思想准备,文联主席马烽见到我父亲时说:你何时来,怎么不提前打招呼?显然,父亲以为,山西文联同意接收,组织联系就没有他的事了,他自己并没有与山西文联商议具体安置事宜。
我们看到的这处大院是南华门16号,院子外面的牌子上写着“山西省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院内西面一排房是民革的办公室,东面住着文联另外两户人家。人们从胡同经过,看到我们院的牌子总是很好奇,打量我们的眼光也很特别。
几天之后,文联已将庙堂一样的正房上了顶棚,连同东西两侧的耳房,隔成四间,并另盖了厨房。厕所在院子里,公用。
人际的温暖也慢慢有了。
我们居住的大院左侧,有一个小套院,套院里住着先我们几个月来到太原的赵树理一家。我们两家都曾在北京居住多年,但因不住在一处,并不熟悉。
一天,一个身着浅灰色薄呢大衣、个儿挺高的人登上我们家门前的高台阶,还没进门就大声道:“老邢,你来了啊?”爸爸迎了上去。看上去他们很熟,也很随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赵树理伯伯。
他黑红的面色,脸上的褶皱挺深,但人很精神,说是刚从乡下回来。赵伯伯四下打量着我们草草安就的家,和我父亲说:我的书都放在办公室了,家里有两个书柜闲着,搬来你用吧。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们家带腿的家具全卖掉了,现在机关虽配备了日用家具,但地上一堆纸盒里的书,仍塞不进公家给的两个书柜。
过了两天,赵伯伯让儿子二湖、三湖将书柜搬了过来,他自己也乐呵呵地跟了进来。
他的书柜上下都是推拉门,上面两扇是普通玻璃,下面两扇粗看像是嵌进两块大理石。爸爸摸着下面的柜门正想看个究竟,赵伯伯笑着说:“这也是玻璃的,是我自制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得意。
他见我们一家那么感兴趣地望着他,就连说带比画地讲起这仿制大理石的做法。
他说,先弄一大盆清水,待水平稳后,再用毛笔蘸上墨汁,迅速在水平面上画出想要的花纹,然后不等墨汁沉落,很快将宣纸铺在水面上,再把纸平着提起趁湿贴到玻璃上,玻璃的另一面就显出了大理石的图案和纹路,和真的一样。接下去,他又讲了贴宣纸的考究,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津津乐道的神态,心想,赵伯伯真是个有意思的人。
时间长了,才知道,赵伯伯“有意思”的地方还真不少。
每当他的小院传来悠悠的胡琴、笛子声,那就是告诉大家,我老赵在家里。我的两个弟弟和赵树理的小外孙同龄,是一块玩的小伙伴,这时,早就蹿到赵伯伯的屋里在他的身旁雀跃了。
我们大点的女孩儿,也经常禁不住引诱,想到他屋里多站一会儿,听他讲点什么,总觉得话从赵伯伯嘴里说出来特别俏皮、有味。记得明代解缙与财主智斗的故事就是从赵伯伯那里先知道的。赵伯伯讲趣事、说笑话,带着浓浓的乡音,加上他的幽默,总让我们乐而忘返。
父母常叮嘱我们无事不要到赵伯伯家打扰,可谁让他那么有意思呢!
赵伯伯跟他的儿子二湖还有我大姐聊天时,常说起《红楼梦》。那时,我看不进去《红楼梦》,觉得林黛玉太娇气。听大姐说,《红楼梦》里的诗词,赵伯伯背了一段又一段,并给他们讲解诗词的意思。赵伯伯知道我大姐喜欢医药学,就告诉她《红楼梦》里的那些药丸为何那么讲究。
连我妹妹遇到不会做的算术题,也去问赵伯伯,因为他总是有问必答,耐心和蔼。有一次他告诉我妹妹,题的答案可以告诉你,但步骤不能说,我用的是土办法,你不能学,学了就入了旁门左道,你们老师该对我有意见了。
那时,我们正是很有求知欲的年龄,赵伯伯对我们是个谜,我们很难想象他有什么事是不知道的。
我还向赵伯伯学会了搪火炉。赵伯伯家厨房的灶火很特别:一个炉膛,大、中、小三个火口通过烟道串在一起用。外面炒菜时,中间的熬稀饭,里面的温热水,炉膛不大,火很旺。赵大娘告诉我:“我们家的火炉都是老赵搪的。”
快入冬了,我妈不停地嚷着搪炉子的事。我自告奋勇承包了三个铁炉子的搪抹工程,他们以为我是冒傻气。其实,我心里有数,师傅就是赵伯伯。
赵伯伯告诉我:往粘黄土里放盐,比放碎麻、碎头发之类的东西结实,炉膛不在于大而在于形状。抹泥的时候不能东一块西一块,要从下往上一层压住一层,从薄往厚。搪好后,不能只烤干或晒干便罢,必须用焦炭一鼓作气将里外烧得通红,等凉了就非常结实。
照他的指点,我搪的炉子使全家大吃一惊。他们奇怪我何时学会了这般手艺?那年,我还不到十四岁。
赵伯伯在家的时间并不多,他经常下乡或外出,但他一回来,院子里的气氛总与平时不一样。
有一次,他外出回来,端着两碗焖面进了我家:“老邢,尝尝老关做的焖面!”老关是赵伯伯的老伴,我们叫赵大娘。爸爸一边吃,一边说:“不错,不错。”赵伯伯听了很高兴。他说:“我出门最想念的就是老关做的面。”边吃边说起山西人的面条有多少种做法和吃法。后来,我们姐妹几个都学会了做焖面。
从爸爸的口气中知道,他和赵伯伯的交往并不深,后来还提到,在“反右倾”、批判“中间人物”的时候,爸爸参加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的批评赵树理、邵荃麟的扩大会议。尽管他早就意识到那些批评很过头,但以后的环境、气氛使他从未正面对赵伯伯有所表示,他内心多少有些不安。未承想,这一切早就在赵伯伯哈哈的笑声中化解了。
多年以后,一提起赵伯伯,爸爸总是感怀他的心胸宽阔、为人厚道。
“文革”开始,赵伯伯最先遭殃。他家门外贴满了大标语——名目很多。我因为热衷于在学校闹革命,回家很少,没有看到赵伯伯被抓走游街、批斗。但我知道,有一次造反派批斗他,让他站在摞起来的桌子上,然后踢倒桌子,赵伯伯摔倒在地,断了三根肋骨。
以后,赵伯伯在家的时候就多了起来,我每次回家见到他,都觉得他衰老了很多。
在这期间,我们家也“沦陷”了。各路人马来了去,去了来,抄了又抄,好像谁家都怕落后。父母索性躲到外面去了,家里只留下我们姐妹兄弟六个和我们的继祖母。那年我大姐18岁,我弟弟才7岁。
有一天深夜,院里一阵狗叫,我们被惊醒,撩开窗帘的一角,一看,好家伙,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叫我们开门。就在这时,赵二湖从套院翻墙过来了。他后来说,不开小院门,是怕引狼入室。
二湖那时年方二十,他摆出一副男子汉的架势,对那伙来人说:“人家大人不在家,家里都是女孩子,你们有事白天来,要不,传出去对你们不好。”二湖交涉之际,其他的邻居也陆续出来帮腔,这群人才悻悻地撤出大门。
事后,我们向二湖表示感谢。二湖说:“我睡得死猪一样,我爸夜里睡不着,听见外面有响动,把我推醒,让我过来看看,说你们家多是女孩子,大人不在家,别出什么事。”
赵伯伯那会儿因肋骨被打断,正犯胸膜炎,哮喘病,一夜一夜不能躺着睡,只能坐在火炉边。没想到这位病殃殃的老者,竟成了我们的保护神。
1969年年初,我同赵二湖等一起到洪洞县插队。赵树理伯伯却受到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他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年仅64岁。
赵二湖在他父亲昭雪后又生活了40多年,于2021年4月6日病逝,享年74岁。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校对 | 谢志忠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f640d6fe-fec6-411d-acd4-5f04445865b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