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特稿|王家声:世上再无刘逸生
文/王家声
刘逸生(1917-2001),广东中山人氏,知名学者、新闻出版工作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以《唐诗小札》《宋词小札》《龚自珍己亥杂诗注》等作品名世。当下五十岁以上的文化人尤其广东文化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他名字的。人们说,他的《唐诗小札》哺育和影响了几代人,这话一点也不为过。

这些年,关于刘老的介绍和回忆已有不少。他是我老丈人,在他的晚年,我们有过一些接触,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但我毕竟不是其儿女,全面的回忆和评价显然不适合我去做,而这也并非本文的初衷。这里,我想从一个侧面,讲一点“如烟往事”,检视一下当今学术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应当从刘老身上学到些什么。
奇人·奇事·奇书
刘老出身贫苦,幼年丧父,由寡母带大,历经悲苦。他做过鞋匠、木工、排字工、报社校对编辑……书读到高小但没有毕业文凭(年长后才入读并毕业于香港的中国新闻学院)。他的父母弟妹中没有谁与“文化人”这个词沾边。像这样完全没有“家学渊源”的人,几经挣扎奋斗,终成大器,一定有着异乎常人之处。
首先,他是个奇人。他的勤奋、刻苦几乎到了极致,好学到了痴迷的程度。而学问的广博渊深和涉猎的方面之多,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试想,一个鞋匠的儿子,周围没有书本,没有学习的条件和氛围,也没有什么“引路人”,而他对知识的孜孜以求,完全来自“兴趣”,来自自觉的本能。在今天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他曾说过,在当时香港那个地方,在抗战时期复杂的环境中,如果不是喜爱阅读书报和研习学问,他很可能会学坏。也许他的刻苦自励是与生俱来的,但那么恶劣的学习条件竟能造就这样一个人才,很值得今人思考。
据刘老本人回忆,他生于乱世,祖上穷困,母亲是个文盲,父亲在他十一岁时去世,于是中断学业,十四岁开始独自漂泊,先是在香港一家报馆当杂务,给“编辑老爷”“校对先生”跑腿。但就在跑腿的间隙,他抱住报社仅有的一部厚似砖头的《辞源》硬啃下去,一个一个条目地读,日积月累,获取了大量知识。及后,还把《康熙字典》的部首背熟了。从读字典、辞典入手学文化、做学问的人,还真的是“稀有”。而他就是从这个夹缝中突围而出的,这实在是一件“奇事”。其后,他又从排字学徒做到报社的校对、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他从香港《华商报》调任广东《南方日报》,并参与日后《羊城晚报》的创办,任该报编委并主持副刊“晚会”版工作,把“晚会”版经营成熔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炉,深受读者喜爱的园地。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这个园地开始以一种“札记”文体连载通俗的唐诗赏析,各界反响热烈。1961年,这些文章结集而成的《唐诗小札》问世,市面上竟出现“一书难求”的景象:无论青少年学生、普通市民还是国家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纷纷争购。60多年来,这部书被多次重印、再版,历经多家出版社,印数超百万册,堪称“奇书”!他于80年代出版的另一著作《宋词小札》也极受追捧,多次重印。这种“小札现象”无疑是又一创举:它开创了诗词评析“小札”体的先河。同类或近似的体裁不知凡几,但好像至今还没有超过它的。此后作者的另一著作《漫话三国》同样接续了这一传统。


勤奋·精细·严谨
读者们可能没想到,刘老本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看重的其实是一部“阳春白雪”之作——学术专著《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他十八岁时在澳门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己亥杂诗》,十分喜爱,自此便爱上龚诗,反复吟诵,熟记于心。但龚诗典故很多,兼通儒释道,是出了名的难懂,从来没有人敢去注。很多诗句的释义,刘老一直在多年求解。“文革”后期,刘老被借调到广东中山图书馆工作。他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大量的馆藏古籍,开始了注释《己亥杂诗》的攻坚。刘老在自传《学海苦航》中记述,为了弄懂一首四句二十八字的无题小诗,他花了三年时间去追查,其精心精细可见一斑。据他本人统计,注龚诗三百多首,翻阅图书不下千种,工作量是相当大的。1981年秋,《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代表刘老最高学术地位的著作,听说钱钟书先生也因此知道了刘逸生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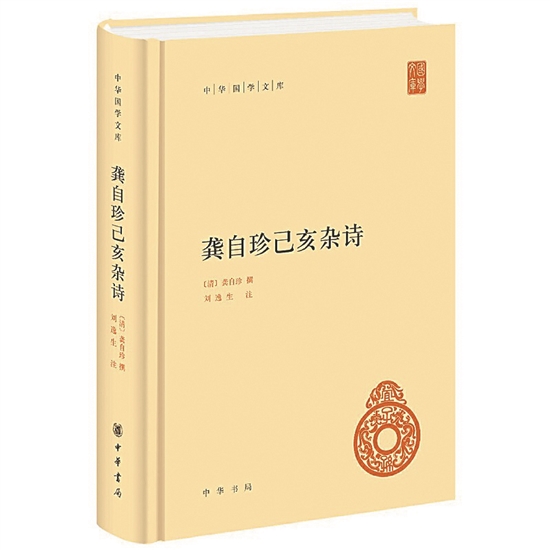
刘老去世后,我承接了他部分藏书。偶然翻阅这些书籍,每每使我一再感受到他的勤于积累、勤于动手。他的每部书中都夹着大量字条、剪报等,剪报都标明出处(报刊名称及年月日),十分方便归类使用和查找。比如一部《亲属称呼词典》中,就夹有《闲话称谓规范》《“先生”的含义》《对亲属的谦称和敬称》《同志·师傅·先生·太太和小姐》等十几份剪报,足见用心之细。早就听说他是个“地图迷”,他留下的一部《世界地图集》中,竟夹有几十份剪报,包括《人口最多和最少国家排名榜》《世界上42个最不发达国家》《世界瞩目的海权之争》等,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图页中,夹着1997年7月北约东扩启动的相关图示,到今天仍具有参考价值和佐证价值。刘老又是一个体育迷,平时会偶尔抽空关注奥运会和各类世界大赛的电视实况转播。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世界各国的英文缩写,我一时答不上,只能说中美俄意四国比较好记,其他真不知道。估计是他想在电视转播时能立即辨认出场运动员的所在国籍。现在终于从他留下的《世界地图集》中,看到他精心粘贴的几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又整整齐齐地手写着几十个国家的英文缩写名称。那时的电脑还很不发达,实在不知道他的费了多少心思才找到的,只能说是“功夫不负苦心人”了。
勤于动手、勤于动脑、勤于用心,这些本来是做学问的基本功,但很多被称为“专家”“学者”的人未必都做得到,有的人甚至时时想着“抄捷径”。刘老做到了,而且做足了,应归入“上乘”之列。一部《全唐诗》合计五万多首,他全部浏览过,并熟知其中曲折,包括哪首唐诗被收入,哪首未收入,同事朋友就唐诗请教,他往往能随口答出。有关唐诗问题向他请教,他当即便能给予说明,不必翻书,因此被称为唐诗的“活字典”。刘老曾亲口告诉我,他某次赴西安参加关于《全唐诗》的研讨会,在会上指出《全唐诗》有40多处错讹,绝大部分被与会学者专家首肯。我想,以他对唐诗研究的深入、熟稔和执着,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勤奋、精细、严谨,确实是刘老钻研学问的一大特色。
“刘逸生小札系列”丛书问世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广东省公布了“百书育英华”系列书目,向各界积极推荐阅读,并要求入选图书的供货不得断档。当时《唐诗小札》和《宋词小札》同时入选,但各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一直找不到这两本书。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两年,读者很着急,作者也着急,但出版单位始终没有动静。我那时正担任广州出版社的副总编,出于职业习惯,突然想起图书的版权问题。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出版法”也公布多年了,但出版者始终是“老大”,作者也不太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一次刘家的茶叙上,我问刘老两部小札和一部《漫话三国》是何时签的出版合同,签了多少年(出版界当时惯例是五年一签,到期再续约)。刘老把大概的签约时间一说,我马上意识到这三部书的出版合同早已过期,而且没有续签。我让刘老把出版合同翻出来,果如所料。此时,我马上表态广州出版社愿意接过这三部书的出版工作,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向社会推出。回去后我第一时间请示了当时出版社的一把手,并得到他的首肯。考虑到图书的内在质量和市场前景,我们给作者开出了十分优惠的版税,同时要求合同期适当延长,高于出版界通常的惯例。对此刘老欣然同意。
刘老在港澳和内地的报刊上发表过不少关于文化、文艺、历史、社会方面的小品文,也有很强的可读性,经过综合梳理,作者又编出了《史林小札》《艺林小札》《事林小札》,并把《漫话三国》更名《三国小札》。《唐诗小札》》《宋词小札》加上这四部小札,合成丛书“刘逸生小札系列”,全套六本。广州出版社以很高的出版效率,于1998年3月全国春季图书订货会上,推出了前三部早已成书的小札(作者作了局部修改增删);又于同年9月的全国秋季图书订货会上,推出后三部新编的小札,在本省和各地大受欢迎。这其中,《唐诗小札》《宋词小札》始终是最热门和重印次数最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三部小札就无足轻重了。《史林小札》等三书,则正好发挥了作者知识广博、通晓历史,上知天文地理,下懂古今异事的特长,让阶层不同、兴趣各异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归宿。看看下列的标题:《秦始皇的高速公路》《秦桧的“币制改革”》《乾隆皇帝的诗恋与‹唐诗三百首›》《小乔不是初嫁》《诗妓和她的枪手》《龙年能生贵子吗》《江山也靠美人捧》……是不是一下就激起了阅读的兴趣?负责录入和校对这套丛书的几位校对员,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承担了繁重的工作,并就书稿的疑难问题与刘老通了数不清的电话。事后她们一致表示,这是迄今为止的校对生涯中遇到的最喜欢的书,相当于一边校对一边上古典文学课和百科知识课,工作完成后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欣赏水平也上了一个新台阶。

“刘逸生小札系列”出版后,我邮寄了一套送给我的导师——中山大学中文系吴宏聪教授,并很快接到他的电话。老师在电话中十分恳切地说,刘逸生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堪称杰出,而且他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做出大量成果,并普及到大众之中,影响面非常广,我们一些大学老师与他相比,应当感到惭愧。我连忙说,岳父自学成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和大学老师没法比。他当即严肃地讲,刚才说的都是真话,并非客套,并郑重地让我转达问候。事后,我把导师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刘老。刘老听后沉默良久,感慨地说,我们这些没有学历的人,在高校往往是被人瞧不起的,想不到你的这位老师这样抬爱,他确实有知人之明。这两位素未谋面的知识者如今都已故去,但他们的心应当是相通的。
现在回想起来,这套丛书的出版应当是“三赢”:读者盼到了自己企盼已久的精神食粮,作者的创作成果及时问世并取得应有的报酬,出版者收获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果皆大欢喜。数年后,广州出版社大度地将“刘逸生小札系列”的版权归还刘家。其时刘老已经去世,但该书的出版合同期未满,我本人亦已退休,转到广东省政协工作。省内有一家出版社希望再版这套书,并增加插图,使之更趋美轮美奂。于是由我居中协调,广州出版社与刘家签订了“中止出版合同协议”,使几部“小札”得以不断延续生命,接连重印、再版,这也可算是广东出版界的一段佳话吧。
《反三国演义》的出版
还有一部书的出版与刘老意外交集,颇值得一提。约在2001年中,我突然接到广东中山市石岐镇一位读者的来信,说从书店买到一本《三国小札》,看到刘老对民国时期出版的《反三国演义》(又称《反三国志》)一书多有贬损,心中不忿。原来他是《反三国演义》作者周大荒的曾孙子周中柱。此处有必要插一段旧话:刘老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是个终身的“三国迷”。他十多岁时考进香港一家报馆当杂务员,第一次发薪水三块银元,全部用来买了一部《反三国演义》。该书八册共六十回,内容皆是翻《三国演义》的旧案,替三国英雄打抱不平的故事。蜀中五虎将关张赵马黄战无不胜,结局皆大欢喜,曹操、曹植、孙权、司马懿等的权位及生死之事,也被一一颠倒。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大快人心。但刘老在《三国小札》中认为,《反三国志》翻案痛快是一回事,“但缺乏生花之笔,……艺术性太差,是此书的致命弱点。”那时我以“冼岱”的化名兼任“小札系列”的责任编辑,周中柱直接给我写信,述说他曾祖父周大荒晚年归隐故里之后,曾“辛勤七载,六易其稿”,在家乡湖南对原作进行了大量修改,与原书比较,内容更详实自然,人物塑造更有声有色,案也翻得更奇。“亲笔手稿装订成册,历经战火、动乱,因埋地五尺而保存至今,无一毁损。”如今看到《三国小札》的评价,伤心气闷之余,十分希望能联系上刘老,“愿将家中珍藏近六十年的作家真迹手稿送刘老先生一读”,如认为有出版价值,则希望他帮助促成修改本的出版,其“全家愿将手稿赠送”,云云。想来这是将要发生的又一件奇事了。

我马上与刘老商量,决定先约见这位特别的来信者。来信者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说自己就是周大荒的曾孙,祖居湖南祁东县,如今带来修改稿抄本的第一册让我们过目。刘老取出上海卿云书局本《反三国演义》,同抄本比照着读,果然是修改了不少,有些还大段修改。再经仔细审阅,当即判断这确是周大荒修改过的本子,而且是很细心的修改。他估计周大荒晚年回到乡间,闲来无事,重读旧作觉得不够满意,于是重新修改,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出版,“不过这本修改过的翻案之作,确实比以前出版的那本更胜一筹,则是无可置疑的。”刘老感慨于周大荒不满足于旧作,归田后辛辛苦苦重新改写,这种务求完满的精神很值得钦佩。他把这个意见直接告诉那位年轻人和我,表示希望修改稿能够重新出版。
2001年9月,《反三国演义(修订本上下卷)》在广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刘逸生先生为该书写了“代序”:《我和‹反三国演义›的一段“鸿雪因缘”》。序中说,这本书深埋地下几十年后重新同读者见面,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而自己同《反三国演义》居然有这样一段因缘,也是十分意外的。“在周大荒来说,他留下了他的‘雪泥鸿爪’,然后飘然去世;而在我,却居然能将他的‘鸿爪’介绍给出版社,还写下这篇序,也算是一种不太寻常的‘鸿雪因缘’吧。”(见《代序》)该书问世后,由于有亲属争夺版权,几乎引发官司,后被出版社化解,但这都是后话了。
回顾刘老奇特的一生,每每令人感慨系之:崎岖的求学路,深沉的学者情,杰出的探索力和不凡的学术业绩,而聚于其一身的种种巨大反差于今确属世所罕见:学历之低与学问之高,报人之博与学者之专,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这里只能叹息一句:世上再无刘逸生!
2021年3月,由广州市文联、广东画院等单位主办的“岭南文艺名家百年百人评选活动”落下帷幕,刘逸生先生以22万多票居百位名家的第六位,说明他在读者心中仍具有难以撼动的影响力。今年是刘老诞辰105周年,也是他参与筹建的羊城晚报社建社65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令人钦敬的长辈。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校对 | 李红雨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c9e5d509-05c1-41dd-a664-d138c63bdeb8.jpg)
161d7fad-6365-4d05-aa02-b4bb708c0c53.jpg)
1ac1b2a5-e4f3-45d5-a098-c644053aa408.jpg)





3c6da453-42f8-43c7-a89d-2b42117efc19.jpg)
f3ad2a51-0290-40aa-b930-48b25f95c29d.jpg)
72329980-dcd2-4cf8-855b-5463ef2cb25a.jpg)
5c937e5a-6f17-4ef1-b7bb-c698d9f1acb2.jpg)
98bcc297-4252-46ea-a8d1-5e62364923e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