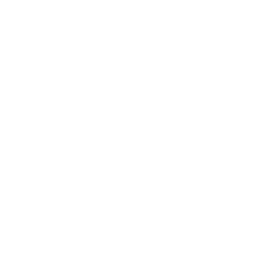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视频】林岗:散文是一种能满足当代人追求精神创造力的文体 | 2022花地文学榜揭晓特刊③

2022花地文学榜揭晓特刊③
12月25日,2022花地文学榜盛典在深圳举行。林岗《漫识手记》(花城出版社2021年3月)获年度散文,特发表其致敬辞、感言、专访——
【致敬辞】
漫谈而卓有识见,手记而自成文体。282则断章随笔,20年来持续思考,叩问自我与世界,纵情于对伦理信仰、社会历史及人生人性的哲理思考。仿若一个思想者在词语密林中的精神漫游。
散文的本质是任心自在,《漫识手记》是很好的诠释。用“漫笔”的形式编织,尽显一派从容、浪漫与生机盎然,让我们面对日常生活时拥有难得的参照,又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散文精神。

大湾区的文学前景:融合、沉淀、再创造
林 岗
今天我站在这里很高兴,谢谢《羊城晚报》和花地文学榜,谢谢教过我的师长、朋友、家人。
在我写的文字中,这本书的内容是我很长时间都没有想过出版的,从动笔到出版可能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如果不是编辑朋友不断地催问“你还有什么东西”,就不会有这本书。
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督促。
关于大湾区文学,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当代广东文学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前30年的广东作家大多出生成长在广东;可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后,广东作家慢慢不能用出生地来确定了。
特别是进入千禧年以后,基本上只要生活在广东的作家,写的文学就是广东文学。这个时期的广东,经历了持续、巨大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作家也是人口流动中的一部分。他们南来北往地来到了广东,以自己的眼光去观察。
从1986年开始,老作家、曾任羊城晚报总编辑的吴有恒曾提出,应该有一个“岭南文派”。后面,隔几年广东文坛就有新的旗帜树立起来,名称有变化,比如叫“新南方文学”“珠江文派”“珠江文明”,包括现在流行的“粤派文学”,都反映了这片土地的新变化。
现在广东文坛还处在变化的过程中,我希望作家们能够慢慢沉淀下来,从这种变化中捕捉到写作的新定位。广东现在有来自全国各地、拥有不同区域文化背景的作家,大家把自己的文学元素带到新的土地上来,又在这里上升为文学的新路径。我想大湾区的文学前景,大概就是将各地文化的融合、沉淀、再创造的前景。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晓楠)

【访 谈】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绍杰
图、视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邓勃 王磊 曾育文 刘颖颖 陈晓楠
1、写作者的“怀旧”:
证明自己在思想上曾年轻过
羊城晚报:您从历届花地文学榜的终评委,到本次成为年度散文作家得主,感受如何?
林岗:这对我来说是个意外之喜。在我的心目中,奖项是有两类的:一类是争得来的,另一类是从天而降的。你们的奖对我来说是从天而降的,令人欣喜。
羊城晚报:关于本次获奖的文集《漫识手记》,您写作的契机和动机是什么?这些发表了或未发表的思考,在您的学术研究、文化评论扮演怎样的角色?
林岗:我在高校里教书。我认为学术思考需要从基本问题开始,从根本处下手。这些大问题未必讲得能马上联系到手头正在做的研究,未必有近在眼前的助益,但长远讲肯定是有帮助的。日积月累的阅读和思考,也可以看作是学术本职的“副产品”吧。
一开始我并没有想过要把这些文字出版。如今这本书所收录的,就是我头脑比较活跃的岁月所思所想的问题,最后形成文字。这便是此书的初衷。
体例上则效仿了前人的方式——比如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就有著作《沉思录》传世,记下他在带兵打仗期间,对人生的思考,格言和信条;弗兰西斯·培根的《沉思录》也是这种体例的著作,影响深远。这些文字读来很让人受益。
羊城晚报:古人有“悔其少作”之说。回看这些曾束之高阁十余年的文字,会不会让您触景生情?它们见证了您个人怎样的变化发展?
林岗:确实有一点触景生情,毕竟年纪大了。要说这些文字对我自己的意义,就是自己人生的一段。有时候回过头来翻看一下,自己挺感慨的:人生经历过这么一个活跃的阶段,思考着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
我想这也挺好的,一个人在某个时段应该是那个时段的样子,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事,这就是人生。
这次出版,我只是按照内容的相关度进行了整理。我一般不会去改动自己写过的东西。要是放到今天,我可能不会这么写,至少我现在的文风和当时是不一样的。思考的着力点不会像从前那样铺得这么开、这么广,而是更倾向于深入个别问题。
但这些文字至少可以证明,自己在思想上曾经年轻过。具体打开书看看,就知道这是出自一个看起来有点老成、其实还是很有点青春的,那么一个人之手。
也可以看到一个时代迹象:或许不知道路在哪里,也不知道哪个结论是对的,但当时很清楚自己处在哪个点上,知道自己就这样认识问题。
2、散文家的传统:
追求表达在前,选择修辞和文体在后
羊城晚报:从《漫识手记》的体例上看,有前贤的“随想录”“冥思录”“箴言录”传统在前。
林岗:这种片段式的写作还是受到西方的影响比较大,比如巴金《随想录》这种文体更多是西方带来的。中国传统上虽然也有看似相近的形式,但更多是把自己过去的一些记忆打捞出来。
比如顾炎武的《日知录》。从学问上来说,《日知录》基本代表了中国古代片段式写作的最高境界。但《日知录》是透过考据史实而认知前路,它是学术式的而不是人生式的。
其实很难说什么是散文的固定格式。我们对于一个文体的认识,总是要在足够多的样本出现之后,才能够归纳出来。在这个方面还是开明一点比较好。就像苏东坡所讲的,文无定法。文体也无定体。
文学的第一义是表达作者想表达的所感所思。追求表达在前,选择修辞和文体在后。
当然从文学史家的角度来看,总是要确定规范,立下规矩,以方便形成关于事物的知识。对于散文,目前辩论很多。如果从作者的角度出发,可以不管这些辩论,根本不必担心自己写的东西是不是散文。
就像我在写这本书的文字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标题,只是记录了某段文字某段思考的日期,但后来用于出版,这些日期就不重要了,于是才有了标题。
羊城晚报:越来越多学者、小说家、诗人加入到散文写作、出版中。散文何以容易成为焦点?
林岗:新文学运动给散文打开了更大的空间,也将西方的好作品介绍到中国。今天中国的散文写作这么活跃,有这么多人在写,这是秉承了中国文学强大的传统,并将其在当代发扬光大了。
诗人要对语言有触电般的感觉,小说家要有超越常人的讲故事的技巧。这是要靠天赋的,但散文并不需要诗或小说那样高的天赋,更多地通过后天勤奋的训练、阅读和学习就可以做得不错。文从字顺,高中程度足矣,剩下的识见、修辞等靠作者自己了。
所以许多人加入散文的队伍,并不奇怪。再者,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的经济发展成就有目共睹,物质生产大发展自然催生了对精神活动的渴望。散文恰好就是可以满足人们对精神创造力追求的文体。
3、评论家的忧虑:
受众的文学鉴赏力随时间衰退
羊城晚报:在人工智能来势汹汹的当下,写作受到怎样的影响?
林岗: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写诗,应该有一天也能写小说。在未来,很可能不仅有人类的文集,人工智能也会有文集出版问世。尤其是那些比较程式化的文类,如武侠、科幻、侦探、言情、穿越等类故事。人工智能完全可以替代作家,透过一个给定的框架,自动生成为“文学作品”。
但是,能不能写出鲁迅那样的小说?这一点至少目前是没办法办到的,今后如何,有待观察。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人的文学趣味也是变迁的。说不定人的文学鉴赏趣味存在向人工智能靠拢的可能性。我们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这个广泛使用机器和人工产品的社会和时代改造了。
每当回看古代佳作,我深有感触:当代人感官的感受力和敏感度上已经变得远不及古人,不及古人那么敏感、细腻。我们对事物的细微处、对情感反应的敏感度都在衰退,感官比古人迟钝,情感比古人毛糙,于是文学的鉴赏力也随之衰退。
是好是坏姑且不论,这种衰退的表征之一,便是那些曾经被推崇的经典在年轻人那里得不到回响了。
羊城晚报:那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写作?
林岗:我自己的写作,大概是“垂死挣扎”吧。当然我希望我是错的。站在写作的立场,做到雅俗共赏是再好不过了。但对我而言,可望不可及。
我曾经讲过自己的“三本书主义”:一本畅销的书,一本有学问的书,一本为自己写的书。我虽然也出版过几本书,但好像这三个目标都没有实现,都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我很佩服能做到雅俗共赏的作家,比如金庸就是一个榜样。他的武侠小说大众和专业两边都可以接受,都备受欢迎。我从前不大看得起通俗文类,自从读了金庸就改变了这看法。文类通俗不意味着文学水准低下,正如出处并不是英雄的死穴。
羊城晚报:其实,新的经典或许也就是在不断产生?
林岗:是的。塑造经典的最终力量其实是读者,而不是专家。这里的读者不意味着当时活着的那一代人,也包括更多尚未出生的读者。他们不是今天的读者,却是明天的读者。
有些作品在它问世的时代不流行,甚至被它的时代所反对,但最终证明的却是时代的鉴赏出现了偏差。不是作品有问题,而是那一代读者有问题。
所以作为作者,不妨固执一点,不妨一意孤行一点,不妨我行我素一点,总之要顽固、要我执,不必讨好市场,不必讨好与自己同处一时代的人。这个年头缺少读者,不等于将来的年头也缺少读者。读者是生生不已的概念。
4、学者的省思:
光摇笔杆子,那只是“写家”不算作家
羊城晚报:您的教学、研究、社会活动与写作的时间如何分配?
林岗:其实我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笑)。当初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一开始对我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但后来我发现,社会活动能够提供途径,让我从不一样的角度了解社会。益处就是让自己的思考不无的放矢,不闭门造车。这实际上是反哺了学术的思考和写作。
要是只有校园生涯,只在学校教书,当然就无从知晓今天的基层文艺活跃到什么程度。大学校园里有诗,乡镇基层也有诗。许多乡镇文艺工作者对诗的热情,一点也不比大学文学教授差。
羊城晚报:对于思辨性的写作,写短文会不会比写长文难?
林岗:会的。现在一些写作者、学者在写理论文章时候,容易滔滔不绝。这一点上,我认为可以从古人、前辈写文章的传统当中吸取有益的地方。不少前辈的文章,以大量材料作为支撑,用一两句话把问题说透,远胜千言万语。
古人对文字风格从来都推崇以简胜繁,这是一个特别高的境界。我们应该提倡简明的文风,在这个方面上现代汉语应该向古代汉语学习。
今天我们的学术受到了西方范式的影响,似乎篇幅不够就会显得学问不够。这是一种严重的歪风邪气。有没有学问,其实看一两段话就能知大概了。
羊城晚报:有往届的花地文学榜得主认为,当今的写作者都应该成为学者型的作家。作为学者,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林岗:依我的理解,他的看法无非是一个好的作者应该多读书。语体文普及以后,文学的门槛就不高了。入门容易做好难。没有大量阅读的滋润,不虚心向前辈典范学习,操起笔就写将过来,就算有文才,也容易江郎才尽,无以为继。
作者多读书,一边写,一边读,让自己丰富起来,这样才能走得远。光摇笔杆子,那只是“写家”,不算作家。
羊城晚报:今年您在中大中文系荣休。现在还需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吗?未来有怎样的学术计划和写作计划?
林岗:我很高兴自己无意中选了一个有非常好“可持续性发展”前景的职业,不会因为退休而中断。有位前辈告诉我,退了休才是做学问真正的开始。这话当然有几分道理。
如今退休了,离开了繁重的教学岗位,对我来说,正是可以写一点自己想写东西的时候。心向往之,没有不适感。至于写作规划,只能写完再说。
任何计划,一半是人事,一半是天意。我确实有一些学术上的想法,但也要老天赞助才能完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2022花地文学榜】
2013年羊城晚报正式创设花地文学榜,一年一度,对上一年中国当代文坛创作进行梳理和总结,也为广大读者提供最具含金量的年度专业书单。
2020年“花地文学榜”首度联手深圳福田成功举办,今年三度走进鹏城。文学在场,双城呼应,为这座“世界之窗”再开一扇文学之窗,眺望湾区最美文学风景。
发起主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联合主办: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
协 办: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
本项目由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资助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邓 琼
编辑 | 陈晓楠
校对 | 赵丹丹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9c00d44e-0945-4b34-beb9-7777bc79ec9f.jpg)

ef2eabc1-b9c9-4097-90c1-eb4503226729.jpg)
1ac1b2a5-e4f3-45d5-a098-c644053aa408.jpg)
671852b6-213d-4967-807a-50b32c68d716.jpg)

9cf5b368-09f9-4bcb-8dec-829764dd3d16.jpg)
1fee2f82-f3da-4a73-8e7e-53f59c80d813.jpg)
4472359c-1a9f-4cf3-9761-8b3d7ceaf38b.jpg)
2e206a05-1768-4232-9de6-d4ed8f06c558.jpg)
f5028e61-f099-4dcf-ad83-358c5127aa01.jpg)
69e94b66-4d93-4db8-be7a-a862d7dcc553.jpg)
96640127-ce18-4da2-8c0c-50673b565726.jpg)
e776a1ff-415b-4602-80cf-f7bf19c7d23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