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汪泉小说:一以贯之的深刻与清醒
文/张建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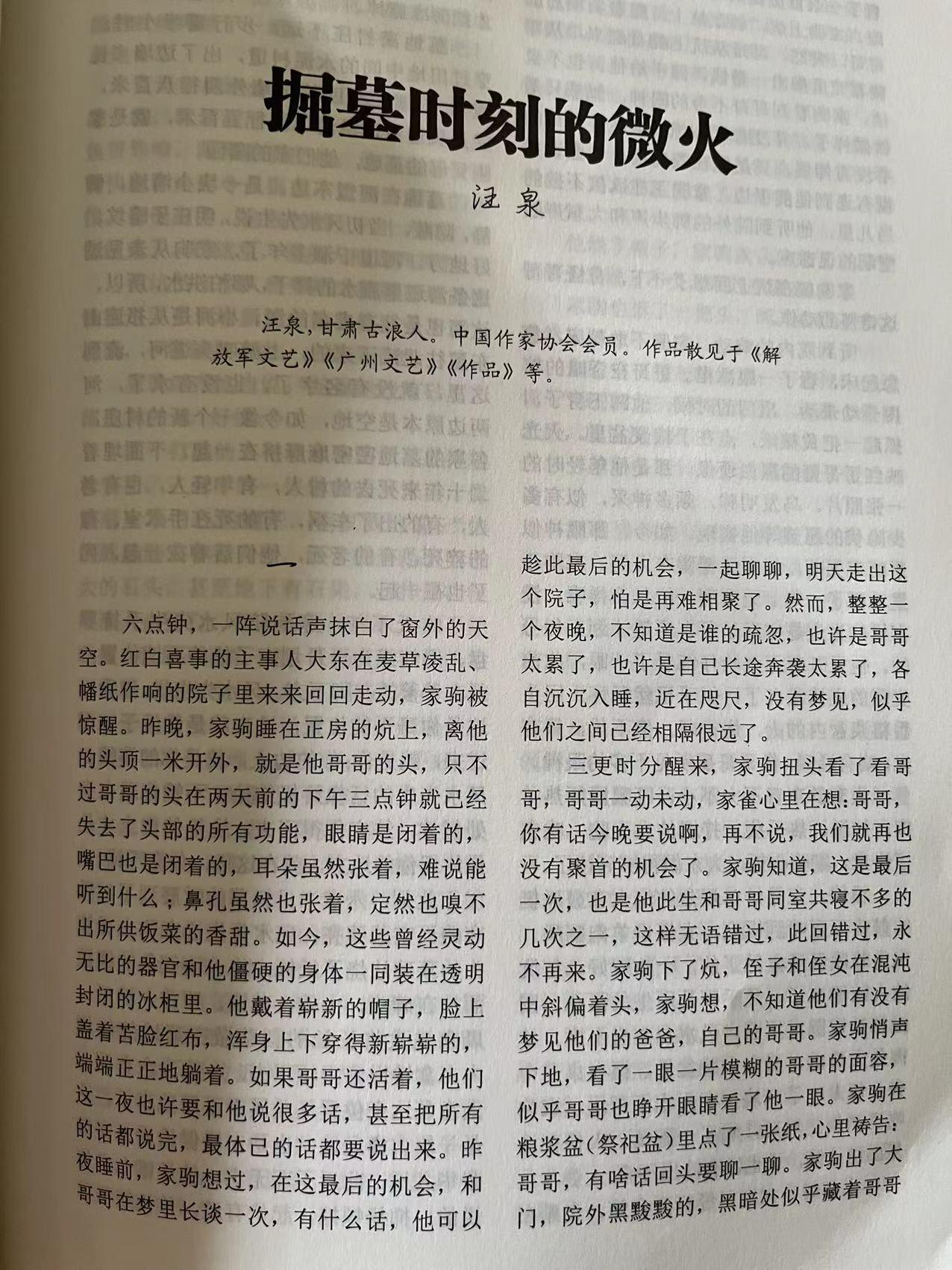
汪泉是甘肃凉州人,挟大漠长风的独特气息,在广州这座城市打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从《共情时代》《敦煌厅的盛典》《燃烧的冰川》到《掘墓时刻的微火》等短篇小说,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近些年他的创作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独具特色。
人类身临其境的时候,往往很难对地域和世界做出准确而清晰的判断,但一个人一旦选择置身事外,他眼底的芸芸众生就会如同浮雕,使其生出历历在目之感。汪泉站在五羊石下,穿过岁月烟尘回望西北,于是那些活灵活现的碎屑就像光柱中浮动的微尘,纤毫毕现,所谓旁观者清是也。
《掘墓时刻的微火》写了弟兄俩的故事,弟弟在哥哥去世掘墓之际,得知哥哥曾经代收了自己的打工收入五十元钱,继而展开了叙述。
小说传承了他小说创作一以贯之的深刻与清醒,从“生”与“死”的视角切入,在一万多字的小说里,以极具张力的复调式结构表现出西北小城那些卑微的小人物——他们的无奈与挣扎,他们的坚强与不屈,他们含泪的温情。最难能可贵的是,这里的每一个人物都光彩夺目,各具特色,绝不雷同。
汪泉的写作,既有非常深厚的现实主义基础,又融合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故其苦难书写不仅真实,更具超脱。说其真实,是因为文中那些充满烟火气息的场面,吃肉、看风水、斩草、打坑,若没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断不能如此举重若轻。
一些画面平淡质朴,但充满乡土社会的气息。
掘墓之前,“羊肉是大块的,盛在大脸盆里,摆在桌子中央。每人吃了一块,有人吃了两块。家驹吃了两块,然后,喝了一碗汤。人们在汤里面泡了馍,谁也没有吃出汗来。”云其超脱,又因其文无处不在的对于生死和情谊的透彻领悟。
如“此刻,哥哥的肉身还躺在棺材里,笔挺笔挺,家驹相信这是哥哥人生最笔挺的一次。……简单而又复杂,甚至如此哲学。天空大地,渺渺人生,同理同在,似乎仰首可见,那根线没有重复,单线,曲曲折折,方向在起点,也在终点,无可避免,最终的方向却是没有方向。”
生死之间,一念归空,万籁俱寂。
他写死亡,哥哥的死是主线,自不必说。写嫂子的死,简直是光彩夺目的一笔,嫂子这个西北农村妇女,在死去的那一瞬间,居然有了神一样的光辉,令人读之垂泪;而甄燕的死,则又始终切合她“文静”的个性特征,生前淡然,死时依然恬淡若水,这样的死恍若庄子离世,无牵无挂,无嗔无喜,命运加之于身的苦难,她照单全收,毫无怨言,令人感佩不已。
他也写爱情,但这种爱情并没有大红大绿喧闹冲动,相识是淡漠的,相知是淡漠的,就连分离也是淡到极致的,但愈平淡愈真切,家驹和甄燕的爱情如此,大哥与嫂子的爱情亦是如此。
面对杀猪刀一样的生活,他们无法坦坦荡荡去追寻爱情,而爱情又确乎真真切切地在他们的世界里存在过。家驹和甄燕彼此属意,但谁也没说,付工资时多给的四十元钱成了甄燕寄给家驹一封最特别的情书,但因哥哥欠债还钱,那代表女孩深情厚谊的四十元,并没有送达家驹手中,红尘男女,就此错过。
唯其如风吹绿波,淡无痕迹,方显其弥足珍贵。
其文虽小,五脏俱全。在如此小的篇幅里,其人物形象却毫不逊色,家驹憨厚而明慧,嫂子勤劳而善良,哥哥麻木但忠诚,就连那个打坑的刘尕宝,也写得栩栩如生,活透出狡黠与善良。
更勿论其以但丁《神曲》作为引子的精巧结构,其准确质朴的语言风格,其圆如弹丸的制局,统统都显示出汪泉驾驭故事的高超笔力。相信假以时日,他的写作一定会穿云拨月,直上九霄。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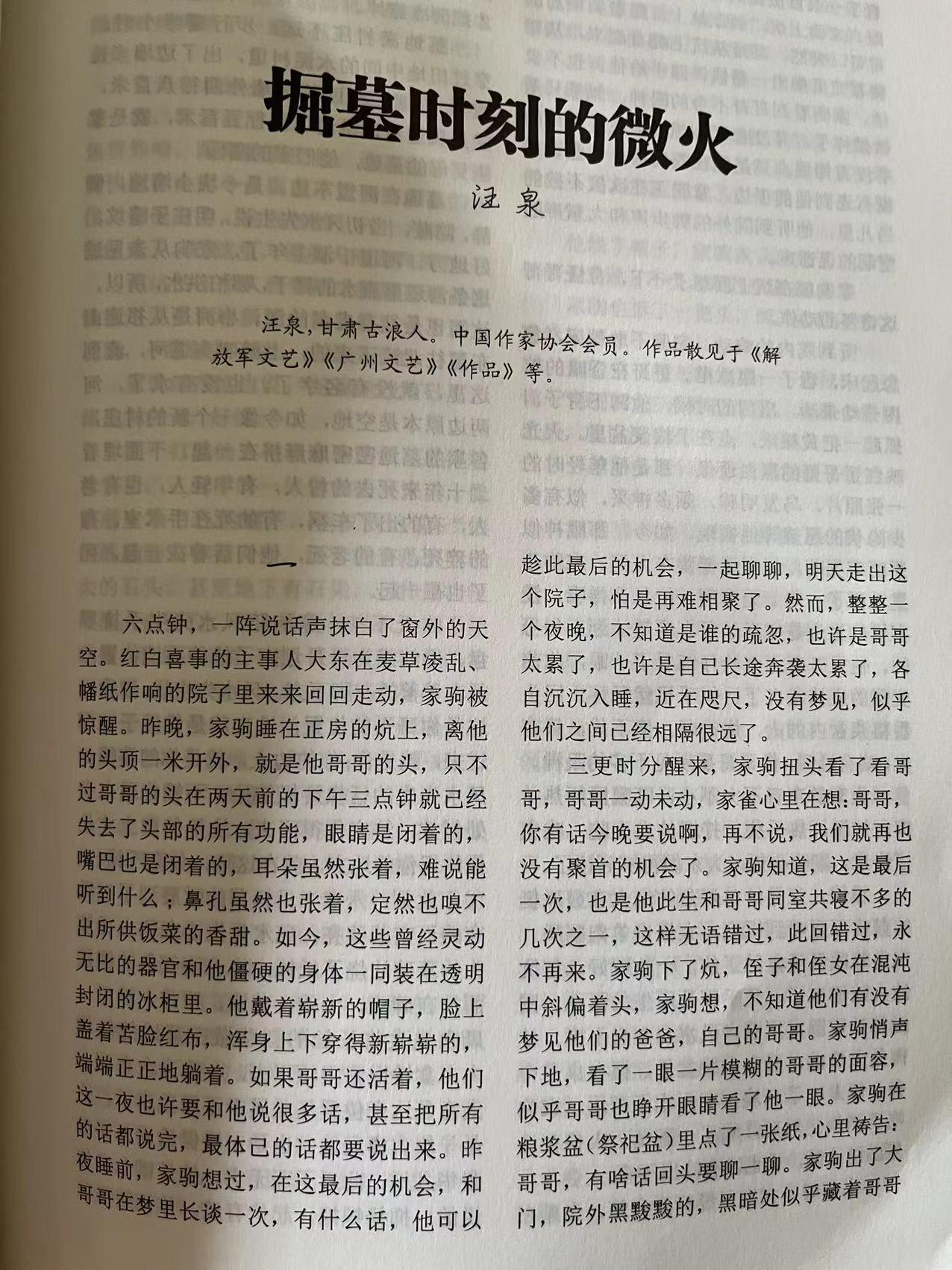
7ce5149d-c1cf-45a0-a71c-67a8a642a366.jpg)

1ac1b2a5-e4f3-45d5-a098-c644053aa408.jpg)


cd8b5658-9c21-4e77-826c-158240ef84ad.jpg)
e8ac6357-da3b-4c94-aebe-bae958e3c288.jpg)
79a4574d-6ed5-4d42-9c53-153fcfd55f7d.jpg)
9092b206-b5a1-4ea4-8586-6699174a0017.jpg)

3495a765-591f-4b0b-82ba-f10ff1b3b7f9.jpg)
f770a4f5-663a-4aea-b2e2-471f72f58958.jpg)
57a5a298-0a58-4270-bfdc-c4ad5234e25b.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