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眼下的全民“网课潮”中,中山大学中文系日前通知各年级学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不能正常到校期间,不跟风开网课,鼓励本科生、研究生们在家阅读与写作。此举于2月17日经羊城晚报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教育部日前亦有明确规定,不提倡、不鼓励、不支持大规模的网课。
开设网课是否适合人文学科?疫情时期的网课热潮是否会加速当下教育方式的转型发展?就此,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文学科可以不跟风开网课,靠个人自觉学习,但这并不适合每一个人。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则认为,网课热反而证明线下交流必不可少。
中大中文系:不开网课,鼓励居家阅读写作
2月13日,中山大学中文系通过邮件、微信公众号及微信群等多个渠道向每一位本科生、研究生发送“关于疫情期间学习安排的建议”的信件。信件中称,按目前广东省教育厅的安排,广东省各高等学校2月底暂不开学,因此同学们返校学习的时间仍不能确定,此后一段时间(估计为30天左右)仍是居家学习时间。中文系长期实行“全程导师制”,学习过程中若遇到问题,同学们可随时与自己的指导老师沟通。
为不辜负宝贵的学习时光,也为与开学后快节奏的教学安排相衔接,中文系向同学们提出了三点学习建议:将写作类学习计划向前调整,完成“大一作文”、“大二书评”、“大三学年论文”、“大四毕业论文”;集中落实“中山大学中文系推荐阅读书目”。其中,大一同学侧重100种文学经典书目的阅读,大三、大四同学侧重50种理论经典的阅读,大二同学兼顾文学经典与理论经典;根据本学期课程表,利用网络资源,如bilibili网站上的北大、清华、复旦等免费人文社科公开课视频合集,预习、学习相关课程。
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向学生发送这份学习建议和要求,是未雨绸缪地提醒学生,疫情期间待在家里,学业不可荒废。该负责人认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解决自己跟自己面对的自然世界、文学世界、人文世界的关系。“人文学科中的阅读、思考、写作是可以独立进行的,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少,让同学们通过自我阅读思考的方式进入到课程学习,相对于以前的课堂教学可能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大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则认为,把“全民网课”改为“全民阅读”,大家就不会手忙脚乱了,哪个家庭都能找出几本书,但并非每个家庭都有网络和电脑的。
北方高校同行:一次自我净化和精神洗礼的契机
与在家上网课相比,不少同学青睐于在疫情隔离时期集中精力读书写作,中大中文系的措施赢得了同学们的支持。中大中文系大三学生张子康向记者表示:“延迟开学期间,系里鼓励本科生独立思考、自主预习,这既有利于我们锻炼学术能力,发现学习兴趣点,也是为了与开学后的教学安排相衔接,可谓一举多得。国家遭此灾难,我们在关注疫情的同时,也应为自己充电蓄力。”该同学收到系内学习要求和建议后,向几位专业课老师咨询了下学期课程内容,利用电子资源提前学习;通过微信读书、喜马拉雅等看书、听书,联系导师并汇报学年论文的进度。
关于人文学科在特殊时期是否开设网课,也因中大此举引发高校同行的讨论。不少北方高校的青年教师纷纷转帖,其中一位南开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转发并评道:“这样挺好,闲暇与放松,是文学最好的滋养。”
该教师表示,这次疫情对教育模式的冲击挺大,身边的老师对网课评价不一。她认为,本来人文学科就是边缘,在网课大潮中可能会再度边缘化,人文学科的老师们需要有定力,坚持人文关怀和核心价值,同时也得对教学设计进行更新迭代,以学生更喜欢的方式来传达。“各个学科性质不同,在线上课的必要性和适用性也不一样,不宜一刀切。理科的课程,需要老师演示公示,画图,演算,做实验等,适合网上直播。文科特别是文学学科,阅读,思考和写作是主要的学习活动,在线上课的话,以老师和同学的互动讨论为适合。”
中大中文系不跟风开网课的措施经羊城晚报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杨朝清撰文表示,朋友圈里有好几位文学院的老师转发了这条新闻,表达了嫉妒羡慕的态度。“不同的教师,在教育信息化的能力和偏好上会存在着差异,并且,受疫情影响,上网环境与心情也与以往大不相同。此外,有的老师滞留在乡村老家,上网课面临着诸多限制;而有的远程教学软件操作起来不便利,也会给老师们带来不好的体验,最终会影响到上网课的质量。”
杨朝清认为,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面临着较大的教育竞争,开设网课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与之相比,大学的学业考核更加弹性、宽松,为“不上网课”提供了基础。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不上网课”并不意味着老师们可以当“甩手掌柜”。对于大学老师而言,他们有更多时间灵活自主地通过课堂群对学生们进行指点与引导。提倡在家阅读写作,本质上为大学生们提供了一次自我净化和精神洗礼的契机,有助于大学生重新发现和认识自我与这个世界。
【访谈一】张柠:人文学科靠个人自觉,课堂教育也有必要
短时间不上网课不影响学业进度
羊城晚报:中大中文系日前向学生发出学习建议和要求,不开设网课,鼓励在家阅读与写作。您如何评价此举?
张柠:我觉得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我们平时把大量的时间用在课堂上,可能把学生的阅读时间挤掉了,其实这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在这么一个特殊时期,留出一点时间让他们补阅读的课,把该读的读一读,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方式未必能够保证所有学生都按要求的来,要是采取放羊的方式,大家都在家里打游戏了,这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说,在学校的时候,教育有一定的强制性,到了点,人必须坐在教堂里面。这也是课堂教育的好处之一,我们并不能保证百分百的学生都有自我阅读的自觉性,可能有20%的人能够用这种方法,也可能另外20%的人不想受到这种教育的限制,对于剩下的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给他们讲什么,他们会比较被动地接受。因此,课堂教育还是有必要性的,人文学科可以靠个人自觉,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羊城晚报:当下网课热,是否和行政规定、学习进度需要有关?
张柠:在特殊时期开设网课,作为教师我也能理解。学校需要一种凝聚力,大学的同学、老师在一起,通过上课的方式凝聚在一起。因此放假也有它的一个限度,如果时间过长了,大家就散掉了。所以通过这种网课的方式,重新让学生有一种归属感,就像在学校里的这样一种感觉,重新让他觉得是开学了。这可能是行政管理人员想得比较多的方面。而对于学业进度而言,短时间内不上网课放在家里读书,也没有多大损失。
部分老师可能有高科技恐惧症
羊城晚报:您所知道的其他高校的情况是怎样的?
张柠:其他高校的情况我不清楚,我们学校还是按照正常的上课时间进行网课教授。下周一,即2月24日起,我们就按照教务处所安排的课程时间点,在线进行授课。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不管是微信群、QQ群还是一些教育机构提供的平台,都得必须在线。另外一个情况是,在线授课提供给学生的方式还是多样的,学生可以在网课的现场,也可以通过重看录像、重听录音的方式回头补课。
羊城晚报:不少高校教师对网课评价不一,您怎么看?
张柠: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高校的老师也是多种多样的,大部分老师还是和这个时代比较接近的,而有一部分老师可能有高科技恐惧症,甚至一些老师连微信也没有,不用微信。他们可能对这种在线教授的各个方面都不大习惯,还是习惯比较传统的点对点、人对人的教学方式。我想对我来说没什么,我直接在QQ群里面就可以开始讲,学生愿意看录像视频,我觉得都可以。

立志研究光听老师讲课没有用
羊城晚报:作为中文系教授,您如何看待个人写作、阅读、思考与课堂的关系?
张柠:课堂讲授的是一些基础的内容。比如我所在的文学系,中国文学史可能一般在学校里一个学年教授完就能掌握,基本掌握上要点。要是只靠自学,要花上更多的时间和功夫。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一些人是天才,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掌握。但课堂教育除了强制性,也有一个省时间的特点。课堂上可以在短时间内把一个人要花上好几年都不一定能够掌握的知识传授下去。
所以我觉得基础课堂教育是比较重要的一种方式,在我们这种师范大学,特别强调基础教育,要听老师怎么讲,才可以去跟你未来的学生去讲。那么写作研究就是另外一个层次了,一般来说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要到了大三大四以后。如果学生立志研究,读研究生读博士,那就还得靠他自己去读,光听老师讲课是没有用的。
羊城晚报:在高校各专业中,人文学科学生课时较少,自由时间多。这和人文学科的学科特点有怎样的关系?
张柠:当然是有关系的。人文学科的一大特点是阅读量比较大。比如说文学,阅读的内容是没有底的。唐代文学文学史讲完了,也只是掌握一个纲要性的东西,往后还得花多长时间去读。比如唐诗,一般读选本就可以了,但作为研究者,不能只读选本,没有读过全集,怎么研究唐代的文学家?所以,人文学科希望学生在学校在掌握了基础知识、基本方法之后,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力气去阅读,所以做人文学科的人,终生都在阅读,终生都在读书,像我们都快退休了,还在补课还在读,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里面它涉及的面阅读量太大,材料太多。
理工科比较适合网课
羊城晚报:有高校教师认为,这次疫情时期的网课热加速了各个阶段教育方式的转变。您是否认同?
张柠: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传统的教育方式肯定要发生一些变化。比如我们现在在课堂上课,就和传统的课堂不一样。过去,老师要是博闻强识型,大脑里装满了知识,随口就能说出来,学生会对你很佩服。而现在他们不一定佩服你了,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在上课的时候,面前就摆着手机和电脑,他们随时都可以把你要说的例子搜索出来,你要是说错了,他们还会纠正你。所以靠博闻强识的方式传授知识,在今天已经不行了。要是老师在课堂上讲出来的内容,是学生在搜索上按回车键搜不到,学生才会觉得老师牛。因此这个时代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对老师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他形式的教学方式也可能越来越多,比如在线远程课堂,等等。但是我觉得面对面的教育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要不然,名牌大学这个概念就没有意义了。大家都可以不在北大清华读书,直接看视频就可以了。但是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在校园里读书,和老师面对面地交流,和自己去看视频,完全是不一样。老师授课,综合了即时性的演讲,表情、动作、眼神以及各种肢体语言,甚至一个老师的气场,尤其是人文学科的老师,也是传递好的大学人文内容的重要环节,它都是属于大学内容的一部分。这种内容不仅仅是白纸黑字的、图书馆里的那种知识。所以,我同意教学方式的多样性,但面对面的教育方式不可替代。
羊城晚报:在不少视频网站都有各大高校或培训机构的网课视频。您如何评价网课这种形式?
张柠:一般来说,网课适合一部分人,比如说北大的罗新老师讲历史特别好,没有条件到北大听课的人,就可以通过网课形式听他的课。但我觉得网课也就是听听而已,并不是像读一个学位那样深入,如果是要了解一点信息,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搞过网课,你就知道它实际上一套套程式化的东西,并不能让一个老师面对听众自由发挥。比如说,它会要求每十五分钟要有一个知识点,这对于讲授文学而言,这样一种机械化程式化的设置是不成的。我个人很反感。人文学科的老师在讲授的时候,对于某个问题特别有感觉,可能会放开讲得多一些,课堂上有一个比较自由的节奏在里面。所以网课我觉得还是门外汉,或者是外行的人去听个热闹还是可以的。
羊城晚报:与人文学科对比,网课形式是否适合理工科?
张柠:对,数学也好,物理也好,他们确实是有知识点的。他们的知识体系,也是由这些知识点和模块构成的。可能社会科学里的某些学科也能这么做,但人文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通过某个点了解其他知识、其他领域,触类旁通,老师在讲授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均衡的节奏。所以你用网课的那种模块式的设置,就很难。你在网上听你也听不到这种感觉。我觉得,与人文学科对比,理工科还是适合网课的。
【访谈二】杨早:网课热反而证明线下交流必不可少
羊城晚报:作为曾经的中文系学生,您如何看待个人写作、阅读、思考与课堂的关系?
杨早:仅就人文学科而言,前三者跟课堂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能不能成才,上不上课并非关键。
羊城晚报:人文学科学生课时较少,自由时间多。这和人文学科的学科特点有怎样的关系?
杨早:王瑶先生说过一句话:“人文学科是平的。”我理解这意思是人文学科的方法不难掌握,难的是走到别人没有走到的路上去,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逊于师,共同研讨,互相启发最重要。
羊城晚报:有高校教师认为,这次疫情时期的网课热加速了各个阶段教育方式的转变。您是否认同?
杨早:对于嚷嚷了很久的网课“推动教育变革”来说,或许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尝试吧。不过,考核机制不变,我不相信会带来本质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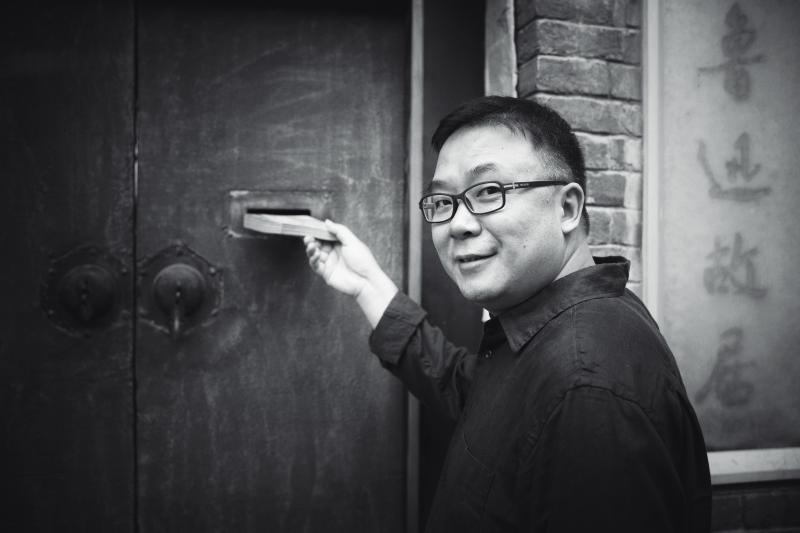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这种特殊时期的网课热?
杨早:就我看到的信息来说,网课热反而向我们证明了线下交流的必不可少,也通过实践,将两者的利弊都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展现。比较中立的结论是:探讨如何线上线下结合的教育方式,应该是将来教育的趋势。
羊城晚报:间接授课与直接授课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杨早:首先是空间感,以及带来的仪式感。这跟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是一样的。在家看电影,太容易被打断,容易分心,更不利于深入地沉浸式感受。其次是互动性。我也上过网课,网课的互动是很难的,不是技术的问题,而且双方专注度不对等,除非网课“直播”化。最后当然是成本投入。成本也是柄双刃剑,一方面肯定是直接授课成本高,另一方面成本高也会让人更珍惜一点。
羊城晚报:您如何评价网课这种形式?
杨早:网课可以让得不到的人得到资源的分享,其存在有非常大的意义。但网课不能替代线下授课,尤其是小规模的席明纳,这一点我也确信。
羊城晚报:网课形式是否适合人文学科?
杨早:人文学科更适合读书-交流-分享,更适合体会当下的真实。其实在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讲知识的意义越来越小,学习思维方式才是学习的真正目标,网课不网课,都是浮云。


9c450fe1-6dbe-4145-891c-72d91d87eb68.png)

d706895c-ea43-4b90-8d6f-607c7cebcb26.jpg)
6c30f0e8-b3e8-43a9-b9eb-d17ccca84a1e16077cd4-98b2-4724-b0fd-4392bd6531e1.jpg)

dcdf33b0-2840-4025-a210-57c7a7adcbef.jpg)
525bc893-28fb-4dcf-a119-87c6f8b6df80.jpg)
ea971f0d-a1b0-4ded-9f7e-06be72af22cd.jpg)
914ed26c-4ae3-4b21-ac06-bd6e8a25ee1d.jpg)



9b230ada-e1cf-475a-9843-aac22dbef692.jpg)
402cc65f-f4de-48e1-b3f8-0acedaf09342.jpg)
c4543f52-bd4b-4e05-82bd-c4c0cdd628a1.jpg)
e74915ea-27e7-4eac-89bc-2bbd97b91c22.png)
230d5c48-ecb2-4489-bb8a-8864bacbc43d.jpg)
53fb3f14-54ec-4252-b504-097f24403406.jpg)
c9c5cb41-f102-4a20-8780-172543956e93.jpg)
a78c40fa-7692-497c-89d5-b8b09e6d584f.jpg)
cba98dac-7b32-4d5b-8fb3-545280d4e0a5.jpg)
b5c0d389-99c6-4991-b74f-40431a21f30d.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