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昊霖
时光荏苒,如小溪潺潺,永不停息;乡愁深藏,像金砂熠熠,日久沉淀。重回故土,那些封尘已久的童年往事像开闸的水,奔涌而来。
小时候是在奶奶家渡过的,那是一个童话般的小村庄。村外是一望无际的湖水和大片的果林,湖边稻田绿波荡漾,田边溪水环绕歌唱。那里承载着我儿时所有的欢笑和梦想。
清澈的湖边是我们的游乐天地,那时的我就像个甩不掉的尾巴,常常跟着哥哥去湖边捉鱼、游泳、打水仗,拾河蚌。最令人乐此不疲的莫过于捉小虾。足下是软滑细腻的河沙,太阳拥抱过的湖水,轻柔地拍打着脚面,暖融融的。湖边漂着大团水䓍,那是小虾藏匿的地方。水草有小刺,我害怕扎脚,只能眼巴巴地杵在岸边。哥哥不怕,总是轻蔑地瞟我一眼,猫腰蹲身,轻手轻脚地蹭到水草丛前,小心翼翼地伸出双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猛地一把抱起水䓍,倏地挺直手臂,使劲往岸上一抛。翠绿的水䓍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伴随着我兴奋的尖叫声落在沙滩上。我忙奔上前,拨开水䓍,大大小小的虾蹦来跳去。我们一边激动地大叫,一边把虾捡进竹篓。傍晚,披着金色的余辉,一路嬉笑地跑回家。奶奶像神奇的魔术师把小小的虾变成各式美味大餐,笑咪咪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
村子里家家户都有一片果园。春天果园是花的海洋,整个村子都浸润在浓郁的花香里。桃花、犁花、海棠花等都争先恐后地爬上枝头,骄傲地展开美丽的衣裙,争奇斗艳。夏天果树们抖落一身繁花似锦,换上清爽的夏装,撑起涛天绿意。雨过天晴,我和哥哥挎上小篮子,跑遍整个果园,采摘果树上生长的一种特有的树蘑菇,它长得似盘盘灵芝,撑开一把把灵动的小伞。新鲜时边缘黄嫩多汁,中间褐色充满弹性,但过一两天就会像木头一样坚硬与树干合为一体。雨后采回家用菲菜炒,嚼来如肉质口感,却又满嘴清香,拌着糯软的米饭,吃得实再是难以停下来。秋天沉甸甸的果实挂满了枝头,果树得意却又不堪重负地弯下了腰。玩累了,惬意地躺在树荫下,稍一伸手就可以摘到可口的果实。丰收时,常跟着爷爷去看果园。爷爷戴一顶大草帽,我带一顶小草帽,爷爷摘果我就摘果,爷爷除䓍我就除䓍。有一次,我们正在树下乘凉。隐约看到有路人在果园边摘果子,我忙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正要过去阻止,一句带火星的“不许摘”已经冲到喉咙,忽被爷爷一把拽住:“别吵,口渴了摘几个果子,不打紧,别惊到人家嘞。”后来我发现看果园只是个象征,淳朴热情的村民们十分乐意把辛苦耕耘的美味果实,送给往来的路人。
村头还有一口泉,泉口宽六七米,其他泉水都冰凉沁骨,它却四季温暖,村里人称它“暖泉”。泉水出奇地甘甜,掺了薄荷汁似的,尝上一口,神清气爽。劳作了一天的村民,傍晚聚在泉边,掬上一捧清泉,冲刷满身的疲惫,老人们认为那是长命百岁的秘方。暧泉是全村人吃水的地方,也是神圣的地方,提到它,村里人无不神色肃穆。泉中还有数条半米多长的大黑鱼,老人常虔诚地说,“这是鱼神,会保佑风调雨顺,平安健康。”每逢过年,乡亲们会选好日子,恭恭敬敬地把鱼神“请”出来,暂放到古老的大缸里,点香供奉上,把暧泉清理干净后,再恭恭敬敬地放回去。这时候孩子们也能分到酥饼之类的好吃的,这是我们盼望的快乐时光。平时,暖泉边会有洗衣服的辛勤的村妇和嬉闹的孩子们。
仲夏夜,微风清爽,蟋蟀低吟,村里的人都聚到打谷坪,圣洁的月光给万物镶上柔和的银边。男人品着茶,女人唠着家常,孩子们穿梭嬉闹,我则喜爱翘腿仰卧,遥望苍穹。无数繁星你推我挤地拥在浩空上,仿佛墨蓝色的玻璃上撒了一把碎钻。几颗大而亮的星星挂在夜空,像是天上的人儿提着灯笼在巡视那浩瀚的太空。探出手,仿佛能摘下一颗闪亮的星。伴着神秘深邃的月夜,听爷爷讲古老的神话和传说。“那是蝎子座”,爷爷笑着指向头顶一颗大而暗红的星,“很久很久以前,一只被狐狸追逐的蝎子掉进了坑里,即将饿死的蝎子向神祈求:‘早知如此,还不如让狐狸吃掉,白白饿死,却不能对任何人有益。神啊,让我做对他人有益的事吧,我愿付出任何代价’,说完蝎子就熊熊燃烧起来,越烧越大,永不息灭,最后幻化成一颗耀眼的星,为人们照亮前路指引方向。”爷爷缓缓道,我为蝎子的无私奉献精神深深震撼和感动。
数年以后,满怀着深深的眷恋和热切的期盼,再次回到我那童话般的世界,那魂牵梦绕的地方,但早已不是昔日的模样。
湖边被层层霸道的别墅区密不透风地包裹,大片果林被推倒,曾经叮咚暖泉近乎干涸,大鱼已不见踪影。村子里的年青人都外出打工,一切都那么陌生,只有老人们在村口懒散地晒着太阳,似那美丽神秘村庄零星散落的古老痕迹。再难寻那往日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得的童年桃花源。
清澈的泉水不见了,成片的果林不见了,童年的玩伴不见了,乡民们悠闲的谈笑声不见了。梦里几回重归故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0c00b676-3f16-43e7-b198-eb2d1bb5f6fa.png)

d706895c-ea43-4b90-8d6f-607c7cebcb2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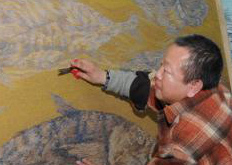






ad18edab-ab41-4fe6-bd24-a7be84f5ac6a.jpg)
c763e6ba-bd19-4406-a18b-d8392030cd29.jpg)

dddd928a-0135-44c4-8e20-dd5e9bd41673.jpg)
a4286da1-774f-42ec-9a6e-49dc488e1245.jpg)
e8f1dd77-ec38-4778-b3a0-84395d9eae11.jpg)
fe965e03-d914-4747-a0c7-db67b6af7317.jpg)
feaf7490-8ace-43e4-a810-2d829674583e.jpg)
779f482e-1def-4d2d-9c99-1b08eb9017f7.jpg)
865ea2e4-237b-47fe-8d64-959273cdc42e.jpg)
2f4eade5-ec9d-44f6-8ac2-bd31e5cf229a.jpg)
2c18ea18-ba18-4cc5-8a6a-1183d6eac076.jpg)
e0d36c6c-6cd5-46c3-bfa7-f873701e5849.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