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洪(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天津市文联主席)
虽然在疫情开始时就听到宗强先生身体渐衰的消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噩耗传来,还是伴随着强烈的震动与刺痛。
宗强先生是我的大师兄,又是合作多年的直接领导。他的学问、人品,正如颜渊所言:“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
从电话中得知先生仙逝,几十年的情境一幕幕闪过心头,一个强烈的印记不断重复着——“本色书生”!
我是1978年考入南开,师从王达津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生。宗强先生是1961年进入王门的,所以说虽为师兄,亦兼师长。我在读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经过宗强先生指导、斧正的。当时在这位“温而厉”的超级大师兄面前聆听教诲,那种混杂着兴奋与忐忑的感觉,思之犹如昨日。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问世,瞬间士林洛阳纸贵。当时,我陪先生去上海,王元化先生、章培恒先生等沪上学界翘楚轮番设宴,席上话题大半在此书。诸位先生皆盛赞宗强先生对那一段历史“同情的理解”,而史料之扎实,文章之赡逸犹在其次也。当时,感慨良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南开的中文学科陷入困境,以致在公开场合有南方学界大佬肆意谤讪。不意数年间竟有如此大的反转。当时之感慨,集中于一点,就是学问、学术的力量乃至于斯!
十几年前,宗强先生的研究领域转移到明代文学,半年之内数次邀我恳谈、讨论。我对明代小说研究略有所知,而他的思考深度其实远远超过。但是,关于《水浒传》作者与写作年代,《金瓶梅》的传播途径,李开先的仕宦经历等,都是虚怀若谷地听取我的意见。
其实,他当时对这些问题已经有相当充分的了解,却仍然愿意听到多方面的观点。我当然也是直陈所见,包括对于不同时段“文学思想史”范式的变通等。有些看法彼此并不完全一致,而宗强先生不以为忤,过后仍然招我品茗畅论。
宗强先生性格偏于内向,但对朋友、对晚辈之热心直如春日。记得1991年,我晋升教授,请詹瑛先生做学术鉴定。由于学校工作的粗疏,给詹先生留出的时间相当迫促。宗强先生出于对詹先生的尊敬,也怕误了我的时机,就亲自去给詹先生送材料。
当时刚刚降过一场大雪,雪融复凝,路上满布冰沟雪棱。罗先生车技很差,骑行在那样的路上实在令人不安。但他不听劝阻,硬是摇摇晃晃上路了。酷寒的冰雪与温暖的热流,那一幕终生难忘,真是“冰炭置我肠”!
宗强先生多才多艺。诗文写作自不待言,而水墨写意犹见功力。一幅“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把《庄子》的精神境界表现得悠远超卓。他与夫人同嗜丹青,相对挥毫,并有合集付梓。南开同仁每谈及此,无不欣羡不已。
称宗强先生“本色书生”,似乎不够高大上。但在我辈心中,能够全心全意心系学术,不慕浮华,远离名利,实在是当今世上最可宝贵的精神。先生的楷模,虽不能至,但高标在前,终如浩浩天宇中的斗辰。
宗强先生精研南华,对迁流之大化早已彻悟。今驾鹤归去,可谓了无遗憾。但在吾侪心中的哀思却是如何销得!
2606f016-d512-4e18-acc5-7e32915697c9.jpg)

76ae16fa-7e93-4d45-82c9-5f4ccc44fbb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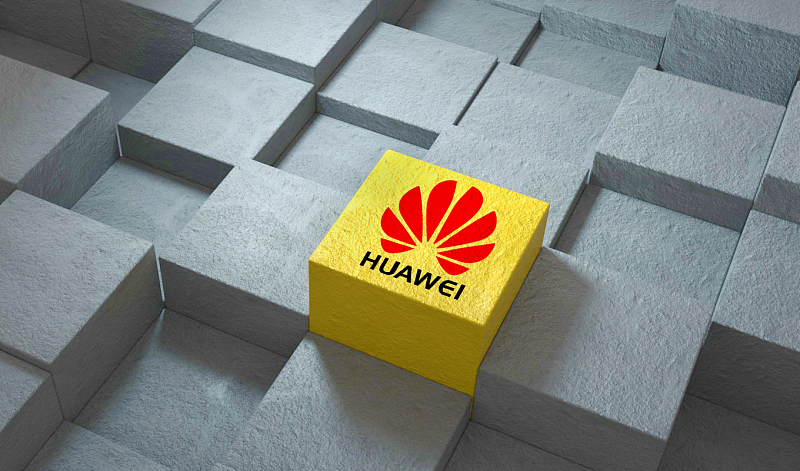

8e1aa36a-f12e-4a7b-b5cc-50958b34d477.jpg)



e47a0f23-a92b-416e-bfc6-7ee01a4c944a.jpg)
24753aa2-aa1c-4441-ab44-11b00deee6b6.jpg)
f81692e4-51a4-4faa-8ce3-dbf5870d29c7.jpg)
d46fa953-e4a3-4738-b6d3-3006312db4fe.jpg)
6bcaa946-5a2b-468e-8561-41a80b978ec3.jpg)


e7cef58b-699b-4f41-bae0-ab88e4dd2cc5.jpg)
4b7f4390-86d6-4e9d-8c2f-3b40202f120f.jpg)
c6280636-49d0-438e-b422-4121affa9d39.jpg)
ae27e40e-feb7-488c-ae18-6a92d3be9cc9.jpg)
ed007825-f01d-4e58-b336-5579242bbb0b.jpg)
f8b2b464-bdb1-40a7-a6f8-09292b33dd84_batchwm.jpeg)
9b9ee957-5012-4740-9f37-73e861dc9fac.jpg)
043ef713-d914-4f25-88a8-ee80cc158ed1.jpg)
58d0a6bd-1753-401e-88bb-95c86bc689fb.jpg)
b4b1a7c5-6dca-47af-91fa-af937a01509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