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兆言

阿来

毕飞宇(左)与李洱
4月中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珠海中心挂牌,莅临的作家叶兆言、阿来在首届“京师南国文学论坛”上结合自己的经历发表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观感,毕飞宇、李洱则给珠海金鼎中学300多位师生、家长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文学课。
叶兆言:
我是在“毒草”中间长大的
我是1957年出生的,“文革”开始时正好9岁。一直到我19岁,这段时期因为我是独生子女,比较孤独,开始大量读书。
我们家的书确实比较多,我父亲(注:叶至诚)爱藏书,有七个书橱。有段时间这些书全部在我房间,所以我那时都生活在书堆里。
我父亲不愿意让我看古典文学,但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他管不到我。对我来说,读书也是随机的,没有人告诉我什么书是必读或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觉得不让看引起的兴趣更大。
快高中毕业时,突然有一种“禁书”让我特别感兴趣,就是当时的内部读物,供批评用的。所以我在上世纪60年代就读到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事实上这本书是改革开放后才正式出版的,不久前我跟塞林格的儿子说起这个事时,他们都不相信。
当时还有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都被称为黄皮书。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都是资产阶级的,是“毒草”。我觉得魅力最大的恰好都是这些“毒草”,有人说自己是喝狼奶长大的,我觉得我是在“毒草”中间长大的。
我跟年轻一代聊天,有的年轻人就说,你们这些“文革”时期过来的人,“文革”是大沙漠你们能看过什么书,但是后来他们会发现,我们年轻时看的书比现在很多大学生都要多得多。想想也很正常,当时我们太无聊了,就像革命者的接头暗号一样,发现什么书大家就传着看,包括香港版的金庸小说。
我记得刚进大学时老师给我们开了一批必读书目,我那时候很狂,一看我就说这些书我都看过,当时同学都觉得我在吹牛。因为上大学前已经读过了世界文学名著,我在整个大学期间的阅读都是比较自由的。
在南京大学,当年的读书氛围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苦。我的同学都疯掉了,太用功了,那时晚上十点要把电闸拉了,只有一个地方有灯,就是厕所,大家就搬着板凳到厕所里看书,而那时的厕所基本上都是堵的,里面的气味真的是一根火柴就能点着,但是大家都在那里读书。我有好多年都是看书看到看不动了才睡,每天读书的时间超过十小时。
今天到处都是书,不存在我们年轻时那种“饥渴”的阅读了,对现在的学生来说,阅读太容易的,反而没那么大的动力了。特别是对于老师开的必读书,大家都很厌倦。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热爱读书。阅读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它是不是名著不重要,是不是排行榜第一第二也不重要,能不能提高你的境界涨不涨你的知识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沉入其中,享受这种阅读。
我成为作家,很重要的原因是阅读给我带来的歪打正着。每一次阅读都会留下记忆,你对书本的抚摸,对历史的抚摸,最终都会成为你写作的细节来源。我的文学梦想就是希望我最后能盖一堆房子,留一堆书,我觉得我跟开发商有点像。 (吕楠芳 整理)
阿来:
文学不能只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
中国人从古到今就有一个博物的理想,比如古文中说要多识花鸟虫鱼,但现实里的中国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差。不信我们到植物园去,估计能说出五种植物名字的人不超过10%。
我们总强调怎么做人,其实做人不光是为人处世,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人生活在哪里?不止是社会,而是更广泛的世界、更广泛的自然界中,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东西,以至于中国人走到自然环境中是陌生的。
中国古典文学一直都跟自然界有联系,自然植物频繁出现在诗经、楚辞。但在后来的文学作品里,自然植物更多的是作为投射情感的意象而存在的,无论是杜甫“恨别鸟惊心”中的“鸟”,还是《爱莲说》中的“莲”,都富有作者情感的指涉。
发展到小说时代,自然就彻底萎缩了。就拿四大名著来说,《水浒传》里看不到自然,都是人在斗争。《三国演义》中很难看到真正的地理,还是人跟人的斗争。《红楼梦》里出现了一些花花草草,但都是人造的园林,最后来来去去都是人。如果同样的题材放在西方文学中就不一样,我年轻时读俄罗斯文学经常“看”到庞大的森林,森林中的树木、花草、果实,虽然没有被赋予特别象征性的意义,但是它们有点像西方油画,让读者能客观认知其中的美,认识这些事物本身。这也是中国文学跟世界文学,或者说跟欧美文学的一个很大的差异。
过去中国有很多文化人都在“格物致知”,人伦、理、法的研究搞了很多,但是对于人们具体所处的地理空间,人们置身于其中的自然环境,这些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甚至是完全漠视。
中国文学起头是多么生气勃勃,后来越来越干枯,只剩下那么几种赋有象征意义的植物。
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人连周围十种以上的植物都不认识,我们应该对这个人感到恐惧。因为他要么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要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自大狂。当大部分人处于对自己生存环境茫然无知的状况中,这个是很可怕的。
过去我跟驴友爬山,我们的驴友真是驴友,背几十公斤的包,背着帐篷。但中国人很奇怪,一旦爬山就只知道爬山这件事情,对路上的东西没有兴趣,这真是驴。他们也带相机,但是相机主要拍自己,或者拍大的自然风光。他们问我说你老趴在地上看什么,我说地上有生命、花草,甚至是各种纹理的石头。
我没有专门做博物学,但是我们到处行走,带一双眼睛看看,回去翻翻书也能认识不少东西。
中国人今天写小说、散文、诗歌,来到了一个无名时代。无名时代是什么?我们写不出自然环境的花草树木、石头、山峰的名字。鸟是不知名的,有人写不知名的小鸟在歌唱,这是什么意思?你居然好意思这么写?
鲁迅是一个很宅的人吧,大家想想《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我家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接着往下又写了鸣蝉、黄蜂、云雀、蟋蟀、蜈蚣、斑蝥,然后又写到植物,“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绕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最后还写到覆盆子。大家算算这文章里写了几种昆虫、植物?如果鲁迅只写不知名的小虫、植物,可以吗?那还叫三味书屋吗?这是基本的作文的方法,我们现在连基本的作文方法都不顾。
我们要看到造物的伟大,认识周边的世界。如果我们的文学还只是着眼于人跟人的关系,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只爱很少的几个人,别的人都是放在栅栏外边要防备的,所以今天中国文学的深刻,在写人的时候往往只能写到黑暗,写丑,写恶,因为只看人跟人的关系,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

9cb2dd33-83eb-4c06-aca6-4f16ae4bd525.jpg)


54caaeb2-6efa-4322-b005-30d88742ee83.jpg)
197f5ccb-2757-4a7c-9c04-aacbc9c36dbb.jpeg)
67e6e8fa-c7ec-4784-99fb-95f4a63c459c85086bea-be3c-4940-9bf3-ea1bfb0fcec6.jpeg)
544c567a-7bde-4016-aba0-ea9534f367f9.jpeg)
e42f1709-55da-49a6-bf67-4cb2f618c148.jpg)


f33aaf31-874e-4bc4-9c7c-53fc0d18be7d.jpg)
1b476fb8-772f-4a60-9611-fe903b86c6c6.jpg)

2e4f249a-be1d-43c0-9e74-8f0098e7fac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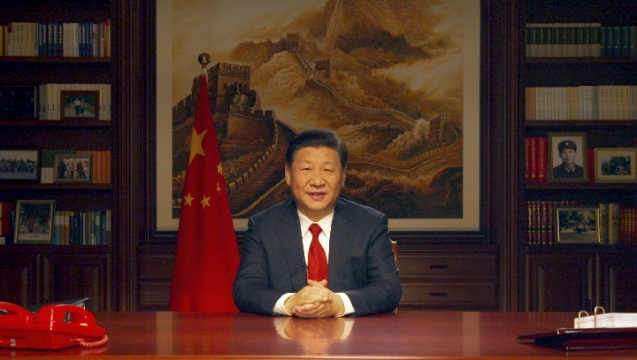
c5f5dad3-0bfc-4901-93c8-2abfad3f9257.jpg)
cdbd18b0-1041-40e4-a0a2-5fc04be56391.jpg)
f3790c8b-d34c-4805-b8f8-42244244240f.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