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10年间发行500期、2000多万字的《打工文学周刊》更名引争议
微议
□谢端平
每逢周日是《宝安日报》之副刊《打工文学周刊》出刊的日子,2019年2月14日这一天读者没有看到那熟悉的刊头题字,取而代之的是“宝安文学”四个字。创刊10年间发行500期、2000多万字的《打工文学周刊》一夜之间改名引发众议。
对于改名缘由,《宝安日报》和宝安区文联的公众号解释:“据了解,将《打工文学》更名为《宝安文学》,源于作家的心声与期望,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呼唤,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有媒体称:“《打工文学》更名为《宝安文学》不是画地为牢、自我设限,而是让根基更稳,让路途更自信。”
“打工文学”源于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时代品牌,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打工文学”称谓从文学概念的范畴来看并没有问题,深圳评论家周思明曾撰文指出:“打工文学比‘劳动者文学’更有本真的意义和真实的价值。这是因为,打工文学是诞生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城市中的独特文化景观:数以亿计的进城打工者白天在流水线上从事简单机械的劳作,晚上下班后常怀‘机器人与木头人’的感叹。现实残酷与文化饥渴激发了打工者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欲望与激情,早期被学者命名的打工文学即由此而生。”但是,近些年来,有人认为“打工”一词似存在“歧视”,但我认为倒觉得“打工”是打工者的真实状态,不必讳言,更没有必要“穿衣戴帽”或“涂脂抹粉”。
也有人认为,可以用“劳动者文学”代替“打工文学”。在逻辑上,“劳动者文学”称谓根本就站不稳脚跟。发挥余热的退休老人,做家务和打扫教室卫生的少年儿童,在柴米油盐中耕作的家庭主妇,不都在劳动吗?真正不与“劳动”沾边的,恐怕只有抱在手里的婴儿,但他们也在吮手指、抓痒痒和配合喂养。所以,我认为,“劳动者文学”一词过于宽泛。
再说,深圳的极少数作家认为要改变称谓,那深圳的绝大多数作家,以及东莞和其他城市的作家们又怎么认为呢?李敬泽在一次打工文学论坛上说过,“打工文学”是一个“营盘”。“营盘”之喻颇形象——有人进,有人出,而营盘总是铁打的。哪一天我们觉得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和崔颢的《黄鹤楼》标题不太好,分别改为“赋得古原植物送别”和“武汉市”,又有何意义?
有论者认为:“劳动者文学从打工文学蜕变以来是怎么样的一种文学呢?第一,是在基层劳动者当中崛起;第二,是新兴的写作群体。”这种说法也得不到打工作家的普遍认可,一是因为“基层劳动”缩小了“打工”的外延,难道写高级白领的作品就不叫“劳动者文学”?二是“新兴的写作群体”纯系一厢情愿,打工文学“新兴”了三十多年,“蜕变”真不那么容易。快四十岁的“打工文学”在其发源和滥觞地被“蜕变”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想还是交给时间来检验。

76022f26-b7f2-4c93-bae2-3863e6bb5050.png)
b12607ee-0ba0-42e4-a28c-1ae249b91ee3.jpg)

622fc7b0-2e08-4483-a76d-d658771a1cfb.jpg)
47255adb-7302-4349-9b08-97f5c2f5f0b4.jpg)
41138cfc-5257-49ea-855b-d87733a133cf.jpg)
6e199c2d-cbd4-443b-b10d-bb6d7ed8d012.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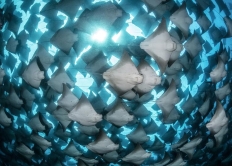


7b9bbb55-c7f2-493f-8f02-15fc3fe5d5a1.jpg)
cf6f0eab-34e2-4c08-a536-ea59f8d73c5b.jpg)

c997710c-6cd2-4f7c-93d8-3bf4c74c26a3.jpg)
f5ff746d-59bf-4e2d-8b39-d96a74e2c545b3005a32-7cfe-4f41-8bbd-6169dcbf969b.jpg)
80ef47d0-4f56-494e-b30c-2ace66298145.jpg)
0fd37345-7a9f-4ef7-91cb-6ae73f3fd436.jpg)
7d10535d-1bd2-4f25-87f3-b70f02ca942e.png)
a5c06a1b-b3cc-4c2b-b0c3-2f513572f844.jpeg)
24a514f1-b710-4dc4-8039-cad3cfdfa547.png)
99e3543d-1bd1-480b-9101-2c1dbb76ff83.png)
bbe2cb99-72b3-401e-9135-7f6632df8387.png)
a7cf900f-0131-47f7-8d1c-d4e72391265d.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