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运长
有一位前辈学者不太正式地说过:当下研究岭南文化,具有较浓的兴趣、较高的热情、较为突出的成就的,往往不是土生土长的岭南人,而多半是那些从全国各地到岭南工作和生活的,就是现在所谓的“新移民”,古代称为“流寓”的文化人。
陈桥生先生《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写就与出版,彷佛又一次印证了这位前辈的判断。这么说不仅是因为陈桥生的确就是一位“新移民”,他是出生于江西,毕业于北大,目前就职于羊城一家著名媒体的文化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书里浓墨重彩着力表现的,就是一批一批的贬徙、流寓者,如何如接力一般地,完成对岭南文明的最初的构建。
“新移民”写“流寓”者,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一种与岭南文明的发生学天然地暗合,体现了某种本质规律和必然性的事实呢?
需要明确的是:岭南文化虽然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概念,但岭南乃是中国的岭南,并不存在一种独立于中华传统文化版图之外的岭南文化。这,大概就是原籍为岭南之外的学者研究岭南文化的某种比较优势所在。研究地域文化如何能够超越某种地方史志观念,让地域文化的概念具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学术价值,这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前辈学人对此有着非常清楚的意识,例如屈大均就一向强调:“入乎广东之内,而必有见乎广东之外”,“入乎广东之内”,必须对该地域得天独厚的土壤、气候、风物、历史等等有切身的感受,至少要有某种“理解的同情”,如此学术才不至于“隔”,才能接地气,有生命的活力。“必有见乎广东之外”,研究地域文化的人,并不是为地方修史志,而是在做一种“为己”的学问,建立自身的观念和价值,尽管地方史志常常也是他进行研究的重要材料。所以他必须建立一套超越于地域所限的,一方面是全国性和世界性,另一方面属于他个人的发明和发现的见解。
陈桥生先生这本《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就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告诉我们:岭南就是中国的岭南,岭南文化其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岭南文明最初的构建,是从先秦到两汉魏晋南北朝,一批接一批贬徙的官员、流寓的文人从中原、江南等当时的文化中心流播到岭南来,与岭南的山水风貌与民俗民情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相互成就的。如此到了唐代,岭南文化的“大宗师”张九龄横空出世,大庾岭古驿道开通,岭南岭北一以贯之,岭南文化就此登堂入室,正式进入中华文明版图。这,大约也正是本书的书名将唐代作为一个历史分界点的理路所在。
岭南的文明风化史,一般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合力发生。一是本地王朝政治,具体地说就是秦汉之际赵氏南越和五代时期刘氏南汉这两个割据小王朝,其中南越是在唐前的,南汉是在唐后的。二是流亡皇朝政治,就是南宋、南明最后在岭南覆亡的小朝廷,这两个都是唐后的。三是流徙、贬官文化。
与前两种力量相比,这第三种力量的作用是更具本质性的,一是规模宏大,参与的人员众多,除了那些史书上有记载的,可能还有更多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二是持续的时间久远,从唐前到唐后,延续千年,从未间断。三是分布广泛,贬徙的文人、官员广泛深入到岭南大地的各个角落,有利于将文化的因子渗透到岭南肌体更加具体、细微的各个毛孔和血管里。事实上,仅就本书研究的唐前时期来看,因此形成的“文化地标”,就有合浦、广信、交州、广州、始兴等等,分属岭南大地不同的方位。

对于贬官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就是韩愈的“赢得江山皆姓韩”,以及苏轼的“不辞常作岭南人”,这两个都是唐后的。陈桥生的《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由于着力于考证、耙疏出唐之前(主要是南朝时期)贬官文化对于岭南文明的奠基性作用,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有了发人所未发的开创性意义。其中有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如谢灵运、范云、江总等,仿佛接力一般,一棒接一棒地为张九龄的出世做准备,令人感慨与惊喜。
作者的考证,所征引的资料,一是采自史书,包括正史和笔记;二是源于研究对象本人的诗文;还有读来更加饶有趣味的,就是引用如地名之类的民间掌故加以佐证,例如广州的一些地名,“秉正街”源自陆贾,“河南”来自杨孚,“客村”、“康乐园”与谢灵运有关,等等。这就更加令人信服地地表明:这些流徙者对于岭南文明的影响,的确是深入到每一个毛细血管里了。
当然,本书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在于建立了一种“为己”的学术见解,为我们深入理解岭南文明的特质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路。而作者的思想观念,又是用一种饱含感情的文学笔调来表述的,这就使得全书思想充沛,而又情感激荡。
例如,人们目下在讨论岭南文化的特质时,经常提到一个说法,就是“岭南风骨”。究竟什么是“岭南风骨”,“岭南风骨”是如何发生的呢?
风骨这个词,大概是与风格接近,说的是某种本质的特征,说一个人的人格可以用到风骨,说一个时代的风气、风尚可以用风骨,如“建安风骨”之类。当然,也可以用风骨这个词来说明一个地域的文化,如“岭南风骨”。风骨的内涵,大约是某种刚健、硬朗的个性,包括一丝儿清高自守,一丝儿慷慨悲情在内。
岭南文化的确是可以用风骨这个词来描述的。陈桥生的《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并没有在各个篇章的题名中标示“岭南风骨”这个概念,然而全书实质上却可以说就是“岭南风骨”的发生学。
这里的学术理路是这样的:岭南文明最初的构建,是由一些贬徙的官员、流寓的文人深入影响下的进程,这些官员和文人的人格特征,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岭南文明的肌体之中了。他们这些人,门阀、地位和名望都很高,文化水准更是一等一的,可算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的个性,当然也从来都是清高的、骄傲的。他们被贬徙、流放,除了各种现实的、历史的等必然性的原因之外,多半也是因为他们过于地骄傲,过于地刚健硬朗甚至桀骜不驯了。同时,由于他们都是有着被贬徙的不幸的命运,有的甚至还免不了要慷慨赴死,他们的个性总有或多或少的悲情在内。这,大概也正是陈桥生在写作此书的时候,行文的笔调常常不自觉地激荡着情感的原因。
“岭南风骨”这个词,可以用一个故事和一句话来进行注解。
据《新会县志·黎贞传》:
黎贞字彦晦,号秫坡,都会里人。生元季。从父学正学于外,既闻孙西蓭贲,即往从之,锐然鞭策于古之人,当路以学行。举署新会训导,辞不就。筑钓鱼台,所居溪上,日徜徉其间,澹如也。适救乡之斗,忤不直者,中飞语,戍辽阳,临行告祖曰:“贞习圣贤之行,读圣贤之书,徒切救人,反辱己躯,虽在缧绁,非贞之罪。”居辽一年,夙夺艰危困厄,而学愈博,识趣愈高,气愈充,议论愈正,阃帅礼之如宾。西蓭贲以事死于辽,抱尸哭,解衣裹之,殡殓如礼,复典衣营葬于安山,为文以祭,闻者莫不堕泪。洪武丁丑赦归,抵家方夜,明月满空,呼舟中余酒,登钓台,赋诗久之,乃叩户入。己卯由荐辟至京,见馆阁诸公,一以礼相抗接,议论侃侃不少屈。诸公相顾谓曰:“斯人可乐就职居人下乎?”例赴部考,托疾不往,促之者曰:“若以老成明经荐,得非耻与后进较末技耶?”不答,竟浩然束装归,赋《出郭》一章诒馆阁诸公。……
黎贞所在的新会都会里,民风剽悍,乡人之间械斗之事在所不免,黎贞为救械斗得罪,因远戍辽阳。恰巧在戍边之地遇到他的老师孙贲孙西蓭之死,将自己行李中的衣服卖掉为之营葬。后由大赦回家,未进家门先登钓台,取舟中剩余的酒,饮酒赋诗,然后才叩门入户。也曾应荐入京,与京城官僚议论侃侃,不肯屈从。他本来是以“老成明经”应荐入京的,而朝廷却要他参加例行的考试才给予授职,黎贞不愿委曲,推托生病不去参加吏部的例行考试,打点行装就出城回家。
黎贞的老师孙贲孙西蓭,时为南海平步堡人,是比黎贞更早的一位乡邑先贤,晚清有“岭南三子”之称的顺德人胡亦常有一首五律《读孙典籍传》:
乱定知真主,书成解阻兵。
功疑拜陆贾,狂乃死祢衡。
文字宁奇祸,君王尚圣明。
如何鼂鼓后,始得见平生。
孙贲主要生活在元末明初,是岭海地区较早的一位有成就的文人学者。他致心于理学正道,好吟诗,于广州南园抗风轩结社作诗,为“南园五子”之首。孙贲在元末时曾任元江西道按察使何真的幕僚,当时的江西道包括广东诸地,治所设在广州。洪武初,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兵取广州,孙贲力劝何真降明,并亲自起草降表,远近生灵得免涂炭,所以胡亦常说他的功劳可以与说服南越王赵佗臣汉的陆贾相提并论。
孙贲以此功受到朝廷垂青,明太祖朱元璋尤其喜欢读他写的诗歌,特授职翰林典籍,“孙典籍”遂成为孙贲的名号。然而,孙贲却屡屡因文字获罪,先是由于与宋濂的文字交往,受牵连而被罢官;后更因与大将蓝玉有文字、书画往来,受到蓝玉一案的株连,终被朱元璋所杀。临刑之前,孙贲赋诗一首,曰:
鼂鼓三声急,西山落日斜。
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
这个故事中的黎贞,在辽阳典衣营葬孙贲,这是渊源有自的。如陈桥生在《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中提到一位南朝宋齐之际被贬岭南封溪的张融:
觊之与融有恩好,觊之卒,融身负坟土。在南与交趾太守卞展有旧,展于岭南为人所杀,融挺身奔赴。
而黎贞的老师孙贲所作的绝命诗,也是渊源有自。《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提到好几位曾被贬岭南的人物,都曾赋慷慨悲情的临刑诗、绝命诗。
“岭南风骨”这个词还让人想起一句话来:“得就得,唔得返顺德。”
《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有言:那些贬徙的官员、流寓的文人,大多经历了政治的起落沉浮,见惯了官场上的风云变幻,因而变得很是“澹如也”。书中说:“这对于岭南当地社会风气的塑造,亦具有垂范作用。更多地经营好自我,不过分热衷功名,也是岭南文化在时间的生长中形成的文化特质之一。”
就是这样,陈桥生《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一书的主要意旨,与我们在现实中对于“岭南风骨”的感受,时常有会心之处。
d8440157-26d0-4824-aca4-0ca2644a9d65.png)

bd70465c-9411-4328-9ea4-69abaee963f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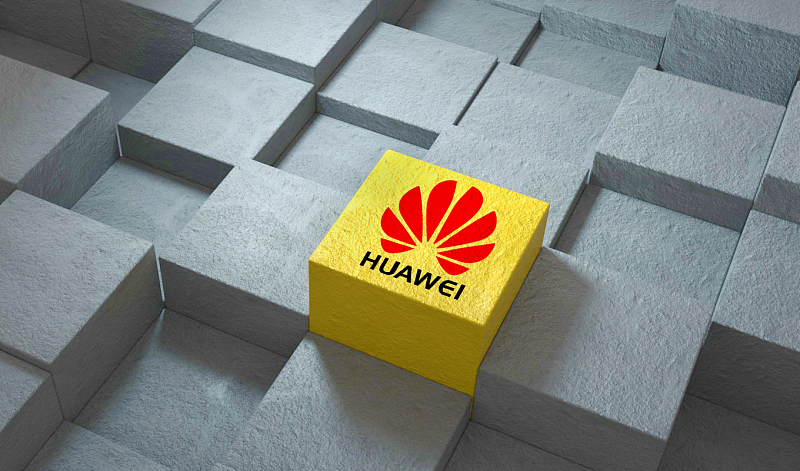

8e1aa36a-f12e-4a7b-b5cc-50958b34d477.jpg)









8383c09f-eaee-4a3d-bb13-5ccd1468d8ce.jpg)
a9814964-b0b0-41f0-986a-19232fdaef5d.jpg)
3ca51285-52c2-45a4-8edf-b3f581577b69.jpg)
562cd385-d2f1-4320-9bad-0299c0da64de.jpg)
3d3aaccb-c543-4a8c-9956-717d35cfbb71.jpg)
dee1cbb9-a9d8-4adb-b365-7e8dcd3383e5.jpg)
a39c47db-ef12-44b8-8700-b09a4c033a87.jpg)
77a8588d-e9a6-45cc-a691-a2ebb4ec3259.jpg)
0d0aedcb-6459-4c5c-a209-264b5ce54aa1.jpg)
c34da8d7-9f06-4d57-aee7-35a31030cd4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