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在康熙年间的“禁海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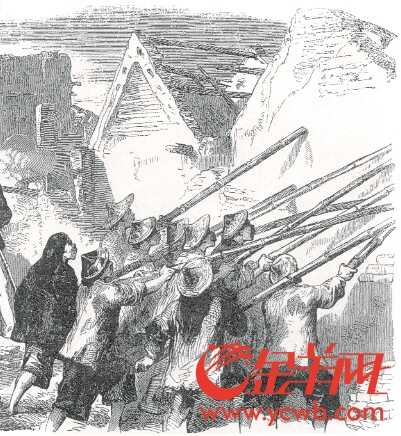
□李开周
一、郑家军得势引起清廷恐慌
中山市旧称香山县,香山县辖下有一个黄粱都。“都”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基层区划,比乡小,比村大,每个“都”包括几百户,由相邻的若干个村组成。面积稍大的“都”,相当于现在的“镇”,黄粱都者,黄粱镇是也。目前这个镇已不复存在,具体相当于今天的哪个地方,有待熟悉地名志的朋友查考。
根据道光年间修撰的《香山县志》,公元1662年,也就是康熙刚刚即位的那一年,黄粱都发生了一场血案:一个名叫班际盛的清兵军官,领兵进驻黄粱都,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当地百姓不分男女老幼,被这帮土匪官兵像砍瓜切菜一样屠戮殆尽。
清兵屠杀无辜百姓,那是史不绝书。
女真人刚入关那会儿,搞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江南屠杀人民何止百万。
女真统治者定鼎中原,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在广东,在福建,在浙江,在湖南,凡是不愿剃光前额、在脑后留一条猪尾巴辫的百姓和士大夫,也被杀了个干净。
康熙年间,三藩作乱,湖广成为主战场,八旗兵一面打三藩,一面抢百姓,以战养战,杀良冒功,战区人民饱受屠戮。
乾隆年间,台湾天地会起义,前有台湾总兵柴大纪在诸罗烧村,后有钦差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在彰化屠村。
再后来,洪秀全造反,湘军与太平天国对峙,为了筹集军饷,激励士气,曾国藩也纵容部下抢掠和屠杀过那些在太平天国治下的百姓。
洪秀全起义之后,广东天地会围攻广州,不幸失败,两广总督叶名琛让士兵捕杀“会匪余孽”,按割下的耳朵数量给部下记功,结果仅在肇庆一地,就有三万平民被杀。
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清军反扑,在青浦烧杀抢掠,轮奸妇女,纪律之败坏,为祸之惨烈,比土匪尤甚……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场血案,发生在康熙元年,当时清朝统治已经稳固,剃发易服已经完结,三藩还没有作乱,天地会、小刀会和太平军还没有萌生,清军为什么屠杀老百姓呢?
起因是一场大规模的“强制拆迁”。
我们知道,康熙即位之时,南明小朝廷虽然已经覆亡,但是东南海岛尚未完全统一,郑成功的后代、部下和朱氏子孙雄踞台湾,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自封“招讨大元帅”,统领十八万大军,水陆并进,攻入江南,不但将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而且势如破竹地收复了三十多个州县,致使满清朝野震动,恐慌不安。
清廷分析郑家军得势的原因,一是得民心之助,二是得沿海之便。早在郑成功尚未收复台湾之时,仅靠金门和厦门这两个弹丸之地,就能挡住清朝举国之力,除了英勇善战之外,更因为沿海人民将粮饷和制造武器的原料源源不断地供应给他;后来收复台湾,一边与日本及东南亚各岛国做生意,一边与沿海人民做生意,甚至还跟驻守东南的清兵做生意,所以才能拥有非常丰厚的物力、财力和兵力,得以与清廷相抗衡。
要想打败郑家军,必须切断沿海通往台湾的物资通道。怎么切断呢?顺治十三年(1656年),郑成功的老部下黄梧投降清军,他给清廷献上的计策是:将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四省的居民内迁,沿海三十里内不许有一人居住,不许有片板下海,如此坚持半年,即可让郑家军队不攻自破。
清廷采纳了黄梧的计策,凌迟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掘毁了郑成功的祖坟,烧毁了沿海四省的船只,将四省居民强制内迁三十里。
但是,内迁政策最开始并没有执行彻底,只有福建一省内迁,山东、浙江和广东的地方官都迫于民怨沸腾,没有真正实施。
二、派钦差大臣到沿海地区实施“禁海令”
顺治十八年(1661年)秋天,由于郑成功大举“入侵”,清军失利,清政府开始制定规模更大同时也更为严厉的内迁政策。从这年九月起,清廷派出钦差大臣,分别到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严格监督“禁海令”的实施,沿海以三十里为限(有的地方以五十里为限),所有百姓一律内迁,所有田地一律撂荒,所有船只一律烧掉。
这年冬天,沿海各省火光熊熊,民房被烧,渔船被烧,老百姓拖家带口、哭天喊地、络绎不绝地搬家。他们原来的住处没了,有的成为兵营,有的被挖成两丈多宽、两丈多深的壕沟,临沟还筑起了四尺厚、八尺高的防御工事。在广东沿海,每隔五里设一个炮台,每隔三十里设一处军营。
康熙即位时,郑家军队退守台湾,暂时放弃了收复大陆的战略计划。那些已经内迁的百姓,有的因为无田可耕,有的因为无房可住,有的因为思念故里,有的因为不适应内陆的农耕生活,偷偷地越过城墙和壕沟,在原来的住处重建家园。
清廷得知内迁居民重返沿海,大为震怒,再次派出钦差视察各地,敦促地方重新强拆。当时平南王尚可喜部下有一个左翼总兵班际盛,奉命逼赶香山县居民内迁。香山县黄粱都地处山区,沟壑纵横,一些不愿搬家的老百姓偷偷藏进山沟。班际盛为了把这些居民赶出来,假造了一纸公文:“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乡亲们放心吧,你们不要躲藏了,只要去报个到,点点名,就会把你们放回去,继续过你们的好日子。
黄粱都百姓信以为真,奔走相告,主动去班际盛的军营里报名。此时班际盛早已准备好了刀斧手,百姓一进营门,就被砍掉脑袋,凡是进去报名的,没有一个活着走出来。
杀完了这些受骗的百姓,班际盛担心其他百姓得知真相,上报官府,影响自己的前程,于是又纵兵大掠,将剩余居民屠杀干净,让士兵运走他们的财产,最后放火烧村。
三、《广东新语》对“强拆”的评价
广东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如此评价康熙年间因为强制沿海居民内迁而造成的惨案:
“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辗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
“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茔而为深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
这些话的意思是,为了防止沿海人民为郑成功提供补给品,清廷派军队划界强迁,命令沿海几十里以内所有居民离开家园,搬往内地,但是官府却不给大家安排住所和耕地。不愿搬迁的百姓被杀,而那些配合拆迁、愿意搬家的百姓,也因为断绝生活来源,被迫自杀,或者卖儿卖女,或者冻饿而死,当局看在眼里,不管不问,把老百姓的命看得连蝼蚁都不如。
屈大均说,因为拒迁被杀的居民大约有几十万,死在搬迁途中的大约也有几十万,百姓搬迁后,官府在沿海划定界线,不让任何人走出界外,因为触犯禁令而被杀死的又有不知道多少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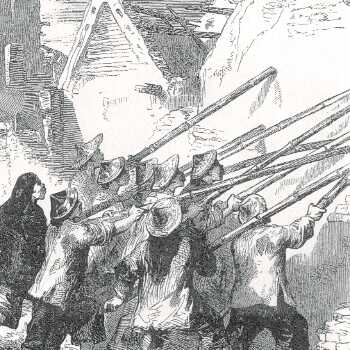

37afdb01-1f2d-462e-ab21-941dce8e8e55.jpg)
d29dce0e-f990-420a-ab47-6a48772edd07.png)
6fca286d-6d61-4650-9dfa-37e106477903.jpg)

2a2450fc-a57b-43b9-ad22-637fc1daee62.jpg)
dfa6990d-fcad-43a8-a87a-941536b72782.jpg)
c9ddb7e8-e194-486f-af39-4ac34cf5b5f9.jpg)
5f281fcd-3bf9-46ec-948a-bcdbc8e4ca1f.jpg)
4fa22fee-aaa0-4a4e-a38d-40c4b5d8b56d.jpg)
7b1fb3e1-a056-4f62-9815-905f32dfacab.jpg)
2cb16e35-f97f-48f4-a436-b373d40449f4.jpg)
031da51e-eab8-474b-9321-5ba3b890872b.jpg)

82a45120-0dc4-42bc-9b14-125dbbe37575.png)
7b599081-d40b-4b6d-b51c-3ee92afc15ce_watermark.png)
8827005e-1dad-42da-a468-9244601f9070.jpg)
3e46049e-8d9d-4256-8e3b-cb2bc77bf100.jpg)
304c0eeb-f100-4b2e-af7e-3699fe66aae5.png)
ffce7f5b-8b91-4d98-a5a8-84eb4f1a2c4f.jpg)
732b692d-4f2c-48d7-8342-e5a8c0e74056.jpg)
41c541b9-c350-4f50-b406-a674aac1d9f0.jpg)
b55b367f-e304-4623-8958-3920cd951bd6.png)
7fec6da1-497e-407a-ada6-202a3592084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