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史的八卦与严肃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郭安瑞于2014年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图书奖”的作品——《文化中的政治》,副标题名为“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郭安瑞、朱星威译,启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研究对象是中国晚清戏曲史,全书分为三个部分:观众与演员,场所与剧种,剧本与表演。作品把剧种研究的主要因素都考虑进去了,但绝非普通意义上的戏曲研究,而是独辟蹊径的一部“填空”之作。
从作者采用“品花谱”、“嫂子我”等边角为主材,剖析京剧的男女性别意识,这种史料的选取和分析方法上,就见新意与深度。
所谓“品花谱”,是一种品评戏曲演员色艺的清代文本,流行于18世纪后期,涉及伶人生平、才艺和北京风月场所的琐谈,主要记录对象是男旦。所谓“嫂子我”,得名于这类戏目中主角上台后的开场白,典型剧本如《水浒传》、《义侠记》和《翠屏山》,刻画以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这类勾引丈夫兄弟(结义兄弟)不得转而与他人私通的女性的故事。
作者所说的“观众与演员”往往是有特定指向的,经常专指剧评家与男旦。这里的剧评家,又进一步限定为撰写花谱的文人才子。花谱作者必定是梨园行家,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判断能引领一时风尚,因此,“年年岁岁出新编”,大受欢迎。花谱撰写总体上围绕着“品”这一排序概念,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作者将之推溯至南宋的文人品味,更借柯律格和李惠仪之论述,着眼晚明时期繁茂的物品鉴赏撰著风潮,得出“文人对物品的书写是对自我世界的重组和规范”的概括。
作者指出,这些花谱并非纯粹鉴赏性的作品。盖自明末以来,士大夫不许狎妓,不得不寄情于优伶,男色之风遂盛。“品”之道,由物及人,就是将人物化。至于以花朵与美人,从色、艺、性情三方面品评男旦,表明了男旦的社会性别女性化的实质。这里既有一种青楼文学话语,也有一种跨越性别、雌雄同体的社会风尚。盖自满清入关以来,江南文化日益趋向阴柔气质。花谱作者对男旦之“花样”描述,不能只认作是无聊的游戏,同时寄托着文人对生命、美貌、自我价值流逝的普遍关切。男旦之微妙处境,最能引起共鸣。
“嫂子我”之类型戏曲,充斥大量色情与暴力,历来是被当作违碍戏的。不登大雅之堂,难入时贤之眼,偏生热闹盛行。作者紧扣《水浒传》等三部戏,分析阐述文本、表演、剧种与观众对社会性别角色接纳之间的相互影响。戏从民间来,首先是娱乐之愿望,后来才自其中发生教化之要求。“嫂子我”原本当是为了惩淫励品,那些出格的女人最后必得大恶的后果。然而,这里头许多的情节,演出淫情浪态的人固然不见得有多少羞耻心,催使着伶人演出这淫情浪态的,自然更离不开台下喝彩听戏的观众。
《水浒传》《义侠记》和《翠屏山》,这三部主题类似、情节大同小异的戏曲,经作者细密的梳理与比较,我们发现,男性由最初的无奈被动杀人到最后的残暴虐杀,女性亦相应地转化成了一种更容易引起大众同情的角色。作者说,“从晚明到晚清,‘嫂子我’故事的发展轨迹引导出两种关于本真时常对立的论述,一个源自出轨而魅惑的女人‘本色’的情欲,另一个植根于争议和暴力的男性豪杰激情。”“嫂子我”里,一方是女子的欲念,另一方是男子的复仇,两方构成的戏剧张力和平衡的不断打破与重新调整,以及公众对两方所寄予的同情的浮动来回,这其中可以得窥两性观念的社会变迁。
本书既然名为《文化中的政治》。那么,政治的影响力体现在哪里呢?对特定剧种的扶持,肯定有官方的导向性。这里涉及清代戏曲的“花”“雅”之争。“雅”以昆曲为首,“花”则起初大多流行于乡村野店,京剧就是“雅之衰”与“花之兴”的产物。乾隆时期编纂的庞大的多卷本大戏《忠义璇图》,就包括了《水浒传》、《义侠记》和《翠屏山》。作者说,这表明清廷在娱乐价值和道德品位之间做了妥协,最终吸纳、挪用了那些戏曲材料。
这种妥协意味着,政治力量以主动的方式参与到了民间语言环境的构建之中,男女性别意识与一个时代相关的伦理道德机制,当然离不开戏曲这种受众面很广的媒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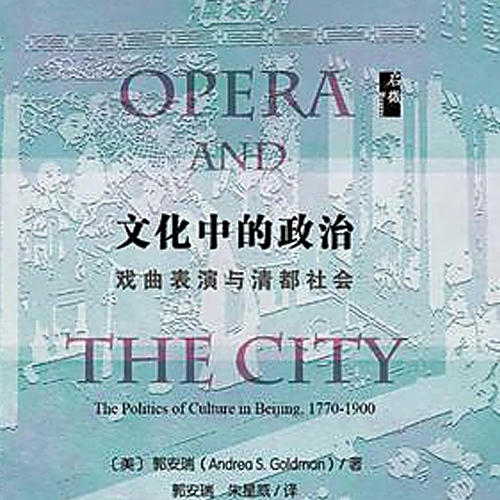

37afdb01-1f2d-462e-ab21-941dce8e8e55.jpg)
d29dce0e-f990-420a-ab47-6a48772edd07.png)
6fca286d-6d61-4650-9dfa-37e106477903.jpg)

2a2450fc-a57b-43b9-ad22-637fc1daee62.jpg)
dfa6990d-fcad-43a8-a87a-941536b72782.jpg)
c9ddb7e8-e194-486f-af39-4ac34cf5b5f9.jpg)
5f281fcd-3bf9-46ec-948a-bcdbc8e4ca1f.jpg)
4fa22fee-aaa0-4a4e-a38d-40c4b5d8b56d.jpg)
7b1fb3e1-a056-4f62-9815-905f32dfacab.jpg)
2cb16e35-f97f-48f4-a436-b373d40449f4.jpg)
031da51e-eab8-474b-9321-5ba3b890872b.jpg)

82a45120-0dc4-42bc-9b14-125dbbe37575.png)
7b599081-d40b-4b6d-b51c-3ee92afc15ce_watermark.png)
8827005e-1dad-42da-a468-9244601f9070.jpg)
3e46049e-8d9d-4256-8e3b-cb2bc77bf100.jpg)
304c0eeb-f100-4b2e-af7e-3699fe66aae5.png)
ffce7f5b-8b91-4d98-a5a8-84eb4f1a2c4f.jpg)
732b692d-4f2c-48d7-8342-e5a8c0e74056.jpg)
41c541b9-c350-4f50-b406-a674aac1d9f0.jpg)
b55b367f-e304-4623-8958-3920cd951bd6.png)
7fec6da1-497e-407a-ada6-202a3592084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