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大众文艺以技术赋能与全民参与为核心,打破创作壁垒,让文艺扎根现实土壤。
广东东莞樟木头镇被称为“中国作家第一村”,吸引了一批中国国内知名作家、学者落户于此,其中多人在国内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有多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湖南清溪村立起21座书屋,文学氛围令人惊叹;宁夏西海固地区出现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诗人、评论家,西海固作家群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
近些年来,文艺创作从精英走向大众,媒介从纸媒转向多元交互,内容从精英书写转向凡人歌谣,形成“人人皆可创作、万物皆可表达”的新生态。
这种新的大众文艺形态,本质是技术平权下文化话语权的再分配,既延续“人的文学”精神,又以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形态激活传统美学基因,构建起传统与现代交融、个体与时代共振的文艺图景。
【羊城晚报·粤派评论】今起开辟专栏“新大众文艺风”加以讨论,首批专家意见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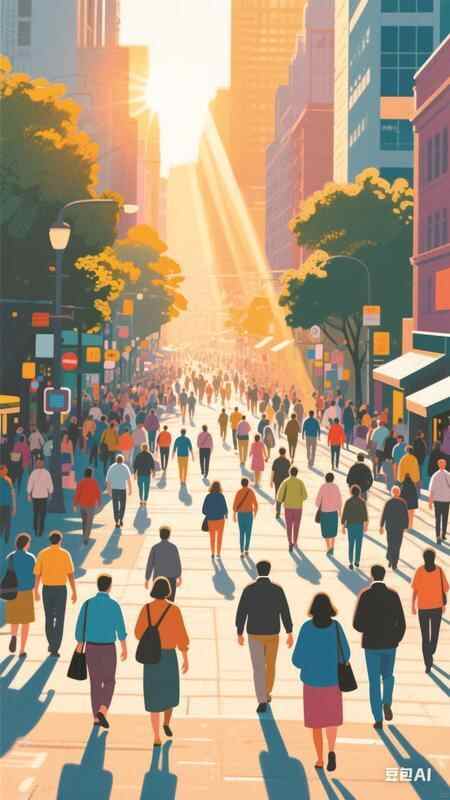
“莞樟路打工作家群”与新大众文艺
文/柳冬妩(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2024年第7期《延河》杂志,刊出《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作者非常敏锐地观察到“新大众文艺已经悄然并蓬勃地从草根和民间兴起并兴盛”:“大众生活,小镇青年,市井人生,摆摊琐记,打工经历,兴、观、群、怨,碰壁撞墙,峰回路转,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劳动者的写作,关于历史的民间记忆,各种圈子、各种样态的新的文学和艺术,它们的蓬勃兴起,标志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和创作正在发生。”
“莞樟路打工作家群”的形成,为“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提供了一个精彩而生动的缩影。
王十月、郑小琼、塞壬、柳冬妩、丁燕、阿微木依罗、李知展、穆肃、萧相风、周齐林、许强、刘大程、阎永群、马昌华、汪雪英、吴诗娴、莫华杰、曾文广、房忆萝、马益林、罗占勇、熊建军等数以百计的“打工作家”,在莞樟路旁边的几个城镇上,留下了各自的“打工经历”“市井人生”。
他们“兴、观、群、怨,碰壁撞墙,峰回路转”,他们不仅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到目前为止,“莞樟路打工作家群”,走出了中国“打工文学”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见证了新大众文艺的兴起。
东莞是中国打工文学的重要策源地之一。1985年,东莞撤县设市,四十年来迅速由一个香飘四季的农业县发展成为国际制造名城,成为全国第15座拥有万亿GDP、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为世界上演了一段炫目的传奇。东莞以制造产业立市,“东莞塞车,世界缺货”一度被用来形容东莞制造业影响之大。
改革开放以来,有超过2亿人在东莞工作过、建设过、奋斗过、圆梦过,“打工作家”就是非常典型的“2亿分之一”,是非常典型的“新大众”。
植根于东莞广阔的创作土壤,不少“打工作家”从产业工人中走出,书写身边的故事,创作了大量的打工题材文学作品,形成了特有的“打工文学”现象,让“东莞制造”有了更加丰富的精神肌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莞樟路打工作家群”强势崛起,从东莞走向全国,成为中国文坛一道亮丽风景。
莞樟路始建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东莞城区与樟木头镇的交通要道,全长43公里,连接东莞中部的大朗、东坑、寮步、黄江等几个重要经济镇区,起于东莞人民公园,止于樟木头镇与谢岗镇交界处。樟木头镇也就是王十月中篇小说《白斑马》“木头镇”的原型地。
《白斑马》原载《十月》2008年第5期,藏策在编选《2008年度中篇小说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时选入了这篇小说,并在序言中说:“王十月在2008年里最有影响的小说是《国家订单》,但我却更喜欢他的这篇《白斑马》,因为这篇《白斑马》更文学一些,让我们看到了梦想的力量。”
在这篇小说里,“木头镇”作为故事发生地,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得到了无限度的延伸,而渗透于其间的时代现实气息,或许比任何一种写作都更显浓烈和复杂。
“打工作家”不约而同地对莞樟路片区某个“地理”进行深度考察,并围绕某个“地理”反复挖掘,像一张网一样打捞起那发生在生态地理上的过去与现在,从而真正使一块平常甚至残酷而丑陋的地理隆起为一块在文化学上再也无法抹去的“文学地理”。
2001年,来到东莞打工的郑小琼,用精细的叙述和渗入骨髓的怀念,一一展开了她对莞樟路片区的追忆和展现,为我们勾勒出了工业城镇的轮廓和幽深。
郑小琼后来离开东莞了,“峰回路转”,她的身份,已经从五金厂女工变成了广东文学馆副馆长(广东文学院副院长、《作品》杂志社副总编),但她所创造或者叙述的东莞依旧存在。
这个当年的打工妹,其诗歌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与发行,曾应邀参加柏林诗歌节、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土耳其亚洲诗歌节、不莱梅国际诗歌节、法国“诗人之春”、新加坡国际移民艺术节、古巴哈瓦那国际诗歌节、莫斯科国际诗歌节、南非诗歌节等国际性诗歌节,其诗歌多次被国外艺术家谱成不同形式的音乐、戏剧在美国、德国等国家上演。
她的英文诗集入围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2023年亚洲翻译奖。长诗《人行天桥》被译介到多个国家。郑小琼在国际诗歌节上朗诵最多的诗歌《黄麻岭》,写的就是东坑镇的黄麻岭村,黄麻岭村已经成为世界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意象。
郑小琼的出现,是“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与蓬勃发展”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和注脚。
诗人、评论家李少君在为郑小琼散文诗集《疼与痛》作序时指出:“郑小琼出身于偏僻地域,却得益于时代开放,能完成和大城市同龄人同样的诗歌启蒙与诗歌教育,接触并学习经典。后来她辗转于异乡,在工业化最迅速的珠江三角洲经历时代风雨的洗礼与个人痛苦感受的抽打沉淀,完成了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的积累,领悟和思考一系列或细微或重大的生活和心理问题。于是,众多外在条件和因素刺激她的灵感和写作欲望,她的天赋与才气得到激发,一写诗,就一发不可收拾,也立即得到诗歌同仁的关注与扶持。再由于网络,她的诗歌获得广泛传播,最后也被主流诗歌界接受。”
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新媒体的产生,不仅是郑小琼“登上大雅之堂,获得广泛认可”的原因,也是整个莞樟路打工作家群形成的原因。
任何一种作家群体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空间和特殊的时代语境。总结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域的文学,历来是文学史家或文学理论家所不愿也不能忽略的。
莞樟路打工作家群的整体崛起,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为研究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极佳标本。在新大众文艺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对这个作家群的形成原因,从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个人、时代和社会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与论证。
“新大众文艺”的喷薄而出,将会重新定义文艺创作
文/孟繁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
百年中国的大众文艺应该是最复杂的一个场域之一,关于大众文艺运动及其争论曾几度成为热潮。
一方面,大众文艺有通俗文艺的含义,它的市场化和消费性特征,在普通消费者那里有庞大的群体。流行音乐、通俗歌曲、畅销小说、商业影视、网络文学、动画漫画、网络游戏、综艺节目等,一直在主管部门和学者的视野之中。讨论的态度大多相互对峙壁垒分明。
大众文艺和人民文艺不是一回事。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扬的报告,周扬是带着胜利者的骄傲和丰富成熟的“工农兵文艺”经验走向会场的,他的报告充满了无可怀疑的自信。他主要阐述的是“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从文艺的主题、人物、语言、形式、思想性、艺术性、普及和提高、改造旧文艺、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等方面,系统地表达了对“新的人民文艺”的理解。
“新大众文艺”从创作实践到现象的提出,是一种文艺观念变革的表征。它是对普通人参与文艺创作的一种积极回应、肯定和支持。它意味着文化权力的重新配置。
文化权力是指在社会文化领域中,某个群体、组织或个人所拥有的能够影响、塑造和控制文化生产、传播、消费以及文化价值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能力与力量。
“新大众文艺”观念重新确立了普通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特别是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创作主体平民化。“新大众文艺”以普通大众为创作主体,他们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而非专业文艺创作者,仅凭借个人对文艺的热爱和兴趣,利用现代技术和媒介参与文艺创作。
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可以称为“新大众”;在内容方面,这一运行态更贴近生活,作品内容更鲜活生动,题材更广泛,涉及日常生活更丰富多彩,也更具有鲜明的个性,更真实地反映出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新大众文艺”,在创作过程中更加注重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同时也能够根据受众的反馈及时调整和改进作品,形成一种自发自主、自娱自乐的创作氛围。
“新大众文艺”的喷薄而出,将会重新定义文艺创作。它可能将专业作家或精英知识阶层独享的文艺创作权力,与普通人分享,确认普通人创作的主体性和自主性。
2020年11月某一天,在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群里,有位教授转发了歌手王琪创作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音乐视频。然后群里很多人一遍遍地转发。那一夜,是当代文学界的大众文化的狂欢节。我还没有见过这个从事“高端”文学研究的学术群体,对一首典型的大众文化歌曲如此地倾心。
2021年8月19日,洪子诚老师突然给我发了一个音乐视频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并留言“一起回到明天”。蔡琴、苏芮、齐秦、费玉清等明星歌手把我带进了久违的上世纪80年代。后来包括刀郎的演唱会,快递员王记兵的诗歌,北京皮村的素人写作等,在知识界都有广泛的认同。
需要注意的是,包括音乐、歌曲在内的“新大众文艺”创作,和传统的专业文艺工作者正在形成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或挑战关系。
专业作家也可以成为“新大众文艺”的一部分,他们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和经验,如果能够放下身段学习“新大众文艺”新经验,从中获得新的灵感和情感方式,专业作家也会以新的面貌获得更广阔的天地。而且,那些有眼光的专业文艺媒体,正在试图改变传统的生产传播方式而另辟蹊径。
“媒体正在成为一所大学”是一个洞见。我们得承认,媒体教会我们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它对我们的观念和日常生活的支配力日益显著。但是,“新大众文艺”也正是因为有了全媒体作为载体,才有可能实现普通人对文艺创作的全面参与。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大众文艺”的出现,既是文艺观念的变革,也是科技革命助力的必然结果。作为一个新的文艺观念,“新大众文艺”将会引领文艺创作向着更开放、更多元也更生动的境地发展。
新媒介、新大众与新文艺
文/唐诗人(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当前,“新大众文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就多数学者的讨论来看,“新大众文艺”是新的媒介技术语境下的“大众文艺”。
从艺术门类来看,“新大众文艺”包括了文学、影视、游戏等各种新媒介艺术;从艺术生产流程来看,“新大众文艺”既是大众创作,也涉及大众传播、接受以及评论。由此,要理解“新大众文艺”的“新”,最关键的是把握“新大众文艺”的新媒介语境、新媒介形式以及新的媒介化的文艺生产与接受逻辑。
所谓新媒介语境,也就是新世纪以来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历史背景。在互联网技术普及之前,文学界讨论的“大众”很多时候也只是一小部分能阅读、会表达的传统读者、图书消费者,很自然地忽视了那些与文学文艺生活没什么关系的普通民众。
实际上,正是互联网技术发现了大众,让大众真正成为了可看见可交流的无数个体。而新时代以来各种全新的数字媒介平台,像微信、微博、豆瓣、抖音、小红书等,更进一步地拉近了普通人与文学文艺的距离,让传统的写作、发表不再是神秘的、高不可攀的事情。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很多普通人通过写作成名、改写了人生命运的故事,通过网络的传播,也成为一种社会效应。比如东莞能够成为打工文学的圣地,这与第一批打工文学作家王十月、郑小琼等人成功故事的广泛传播直接相关。
东莞于2006年开始成立的“中国作家村”,聚集了很多作家、评论家,开展了很多文学活动。线上传播,与线下文学工作,共同构建了东莞的大众写作氛围,也让东莞具有了大众写作传统,这也是我们今天依然能够在东莞发现像温雄珍、曾为民、王瑛等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重要缘由。
新媒介技术不仅是新大众文艺创生的文化语境,也重塑着新大众文艺的媒介形式。媒介技术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工具,它有自己的物质特征,会逐渐影响我们的文艺表达,甚至重塑我们的接受习性。比如影像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大多数青年人欣赏文艺作品的习惯。
这种改变既包括认知层面的方法,更关键的是生理层面的感知方式。对于文艺接受而言,传统注重叙事逻辑的审美习惯,已经变成了强调情动效果的具身体验。大众在新媒介技术的影响下,有了新的接受习惯,必然生成新的审美需求,这反过来重塑着我们的艺术形式。新媒介时代的“新大众文艺”,需要主动调整表达方式,适应“新大众”的情感需求和感知结构。
在新媒介技术出现之前,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时,核心问题是文艺如何通俗化,如何用大众能够欣赏的、乐于接受的语言和结构,这是将大众作为读者、接受者,以大众的文化习性来要求文艺创作者改变写作风格。
但新世纪以来新媒介技术语境下生成的新大众文艺,这“大众”就不只是接受者,而是创作者、接受者、评论者、消费者全链条的“大众化”,这有赖于媒介技术的支持。这不仅仅是网络写作与数字化阅读的问题,更是AI技术支持下的多媒介、跨媒介融合现象。
数字化阅读,让很多阅读者逐渐转化为网络写作者。网络写作者,也借助新媒介技术,成为文艺传播者,甚至成为跨媒介改编的实践者。如大湾区青年作家陈崇正、吟光等,他们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写作者,也在尝试用AI技术将自己的作品音频化、影像化。
技术的发展,已经让传统需要巨额资本、宏大技术支持的机构型媒介融合,逐渐变为成本低、效率高的个体性媒介融合。新媒介时代的大众文艺,是多种形态文艺形式的融合性表达。
当然,我还想强调的是,文艺有其变化的一面,也有其不变的内在面。技术在发展,大众在变化,文艺要意识到这些新变,同时也要坚守一些永恒不变的东西。文艺是温润人心的文化作品,有其文化传承和讲求“真、善、美”的基本要义,也有其内在的艺术品格和人性逻辑。在新媒介时代,适应新的媒介技术、走向新的大众的同时,也应持续强调艺术性和创造性。
从“东北文艺复兴” 看民众的超地域美学趣味
文/刘诗宇(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研究员)
“东北文艺复兴”是个复杂的概念。体裁上,它涉及小说、说唱音乐、电影、短视频等多种形式的作品;语境上,它既是文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既有学者、批评家专业性视野中的一面,也有互联网自发兴起,意图与传统、精英审美相对抗的一面。
目前多篇关于“东北文艺复兴”的研究文章,都认为所谓“复兴”是存在问题的,原因是近几十年来,东北文艺从来没有“衰落”过。这种说法没错,但或许没有命中问题的要害。
大量出自东北的作家、演员、歌手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里,之所以今天仍要谈东北文艺“复兴”,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东北文艺”衰落了,而是曾与“东北文艺”深度绑定、属于社会中下层的阶层趣味在文学、艺术中一度“黯淡”了。
并非所有具有东北文化地理学色彩的艺术创作都属于“东北文艺复兴”,相反,是被纳入“东北文艺复兴”的艺术创作,比如“铁西三剑客”,比如东北风说唱,比如“社会摇”“喊麦”,都在用看似具有东北文化地理学色彩的创作元素,去重新践行、强调属于社会中下层广大民众的超地域性阶层趣味,这才是所谓“复兴”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崭露头角”之后,双雪涛、班宇的创作都不约而同体现出“去东北化”的选择,转而追求一种强烈的城市中产阶级甚至精英美学气质。跟随东北色彩一同消失的,往往是源自童年记忆的关于底层的经验与想象,这或许也能证明“东北文艺复兴”内部强烈的阶层趣味属性。
从这个角度看,其实那些每天挤在地铁公交上刷着短视频、听着流行音乐、跟着流量明星推荐而阅读文学的人们,也许比文学批评者们对一些时代之变或文化现象内部的特质更加敏感,只是他们并没有将其抽象提炼为语言和论述的能力,只能用观看、点赞、转发的形式表达意见;
又或者说,随着互联网放大了他们的声音与诉求,文学研究终于面对了“东北文艺复兴”这样一个对象——不仅作品的内容、思想、形式不再只向传统的精英化艺术标准看齐,评价的标准也一并变得“平民化”;
同时,纯文学研究的合理性虽然不会动摇,但对于新世纪文学史研究来说,传统的只局限于文学内部或某个阶层内部的视野可能即将失效,对文学史的研究必须从代入互联网语境的文化史框架入手。
“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概念从互联网产生之后,在最近一两年已经迅速被文学界“征用”。近些年,老藤等作家的长篇小说中,也都在努力塑造一个文明、富足的当下东北社会,此时“文艺复兴”就不可避免地再度与“经济复兴”绑定在一起。
互联网层面的根植于社会中下层美学趣味,以抽象、土味、伤感、怀旧来宣示存在感,对抗精英话语、主流话语的“东北文艺复兴”,仍然会长久存在,甚至变化为“华北文艺复兴”“西北文艺复兴”也未可知。互联网等新媒介和载体的发展造成的阶层趣味分化,是理解、书写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文学史的关键。
“人人都是评论家”已成为一种新常态
文/周思明(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新技术不仅改变了文艺创作的方式,也对文艺评论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代背景下,文艺评论呈现出了大众化、分众化、互动性、自由性等诸多特点,可谓众声喧哗、争奇斗妍。伴随大数据、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新技术的发展,文艺评论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演变。
不少文艺作品融合了多种艺术元素和技术创新,对文艺评论也提出了更新文艺理论和审美策略的要求;文艺评论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包括职业和专业评论家、自媒体人、用户观众等。
同时,文艺评论的载体和传播形式也变得丰富立体,社交媒体、组织传播、社群传播等多种方式并存,使得文艺评论能够更广泛地覆盖不同的受众群体。这打破了文艺评论僵滞格局,给文艺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网络文艺评论的特征是即时传输,几乎达到了同步品鉴与同步反馈的程度,而且具有强互动性和可参与性,形成了一种黏合性非常强的粉丝圈。其评论主体是匿名的普通网友,形成了未加约束的大众文艺评论,形成了“人人都是评论家”的新常态。
网络文艺评论充分借助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协作,“阅读”更大规模数量的文艺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寻找评论对象。在此过程中,网络文艺评论对于引导网络文艺创作者的写作方向和社会大众的网络审美情趣发挥着自由、直接的引导作用,是对传统文艺评论的有益补充,有助于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从而在重塑中国文化形象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网络文艺评论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其不足也在所难免,比如缺乏文体自觉,即兴发表意见,甚至变成个人情绪发泄,未经严格专业训练的网络文艺评论写作的文体分析与概括往往不够准确,缺乏应有的理论力度和批评识见。
因此,部分评论文字的观点不够公允,深度不足,缺乏见地,影响了网络评论的说服力和公信力,甚至偏离了文艺评论的本质。
无论是传统文艺评论或网络文艺评论,都要守住“底线”,架设“高线”,提升“上线”。不仅要坚守良知立场,抵制低俗、庸俗、媚俗,鞭挞假、恶、丑作品和现象,做好“剜烂苹果”的工作,还应该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文艺创作弘扬真善美,为新时代文艺发展勘误引航。
两者结合,相得益彰,可使文艺评论形成一种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际批评效果,通过相互学习和彼此赋能,共同推动文艺评论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