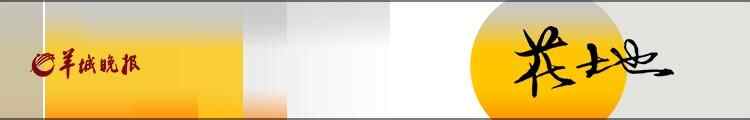
文/陈又新
1
雷州半岛的冬松岛,是我记忆的原乡。20世纪70年代初,我降生于这方被咸腥海风与碧蓝波涛围裹的孤岛。岛上的日子如潮汐般单调,唯有每年三四次雷剧开锣的时节,才骤然如天空裂开一道缝隙——刹那间,斑斓的光从外面世界汹涌灌入,照亮了我们这些岛童贫瘠的精神荒原。
海风裹着锣鼓声远远送来时,冬松小学附近的梧榆树下便立满了翘首的人影。奶奶早早备好了矮凳,粗糙的手攥紧我,像攥住一只急于挣脱的小鸟。暮色四合,戏台前人头攒动,油彩的浓香、尘土的气息与海腥味混杂着扑入鼻腔。
灯光骤然亮起,晃得人几乎睁不开眼,随即丝竹锣鼓齐鸣,高亢的雷州方言唱腔破空而起。我坐奶奶膝上,小小的身躯被巨大的声浪裹挟,初时惊惧,继而如被雷声撼醒般痴迷。
戏台之上,峨冠博带的王侯将相、珠围翠绕的闺秀佳人,陡然撞破了我狭窄如井的视野,仿佛天地骤然延展,岛屿的边界被这华美的幻象轰然冲垮。
戏台之下,人间烟火正浓。卖虾饼的摊子热气蒸腾,那人灵巧地转着勺子,裹着虾仁的面团在滚油里滋滋作响,金黄的脆壳裂开,香气霸道地钻进我的鼻腔。奶奶有时会从旧手帕里小心地数出几个分币,给我买一个虾饼。我贪婪地舔舐着那只小虾,眼睛却一刻不敢离开戏台,生怕遗漏了某个转身或亮相。这方寸戏台,成了小岛唯一的彩色窗口,一个超越咸腥海风与贫瘠沙地的瑰丽出口——幕启幕落间,世界竟如此辽阔。
奶奶是引我入戏的第一人。当《陈世美》里忘恩负义的驸马终于被包拯那一声霹雳般的“开铡”推上虎头铡,她攥着我小手的力道骤然加重,如同要捏碎我幼小的骨头:“做人万不可学这黑心肝的状元郎,忘了糟糠之妻,老天爷有眼,铡刀等着呢!”她眼中跳动着台上包公蟒袍闪耀的火焰,那火焰炙烤着我蒙昧初开的心,第一次将“天理昭彰”四个字,用铡刀落下的寒光刻在了我尚未成形的骨骼上。
爷爷也最爱端坐戏台前,腰杆挺得笔直。包公出场,他浑浊的眼便倏然亮起,如同被台上的星冠点燃。当“包青天”在雷胡激越的伴奏中唱出“铁面无私丹心忠”,爷爷会跟着低声哼唱,枯瘦的手在大腿上击打节拍,沉浸于那刚正不阿的凛然气韵里。
散戏归家,海风拂过木麻黄,爷爷牵着我,沙哑的雷州方言随涛声起伏:“做人要像包大人,心中有秤,骨头要硬。”寒夜星光下,他话语里的重量沉甸甸地压入我稚嫩的魂魄——戏文里的忠奸分明,竟成了海岛人活着的脊梁。
如果父亲也来,他常把我架在他宽厚的肩头,视野陡然开阔。台上演到《状元桥》,寒门秀英卖屋送儿赶考,自己沿街乞讨,儿子最终高中状元、锦衣还乡,搀扶母亲昂然过桥。幕间换景,锣鼓暂歇,父亲会指着浩瀚星空,声音低沉如脚下暗涌的海:“戏里演的都是真人。做人要念恩,要争气!”他粗糙的手指仿佛点破星河,把“孝义”与“志气”的种子,借着戏文的情境,深深摁进了我仰望星空的瞳孔里。
而此时,母亲可能正在灶台烟火气里劳作,亦将“坚忍”二字,如海盐般无声渍入了我年少的味蕾。
当《杨令婆监军》的剧情在台上铺展,白发杨令婆以智谋消弭边关烽火,促成宋邦与古家堡重修旧好。台上旌旗猎猎,台下父亲亦神情激昂:“这叫疏不间亲!再大的仇,打断骨头还连着血脉经络!家和万事兴,国和才太平!”
舞台上的忠勇大义,家国情怀,经由长辈们朴素而炽热的诠释,如同滚烫的烙印,在我懵懂的心里滋滋作响。这些戏文里流淌的处世之道,在贫瘠的海岛上,成了滋养童蒙最丰沛的泉眼——它们无声地渗透,悄然塑成了我最初的轮廓:知是非,懂恩义,慕忠良,怀家国。

2
后来负笈离岛,求学于喧嚷都市。海岛的涛声与戏台的锣鼓日渐遥远。然而当异乡的夜晚,独对如豆孤灯,或穿行于城市令人窒息的钢筋丛林时,那些镌刻在血脉里的雷剧唱段便会在灵魂深处骤然炸响。
学业困顿、人际倾轧、世事纷扰的迷惘时刻,包公那一声石破天惊的“开铡!”如利剑劈开迷雾,爷爷那句“心中有秤,骨头要硬”的低语便如礁石般浮现,支撑着我不至在浊浪中沉沦。
多年后我重返故岛,恰逢村中年例戏开场。戏台依旧面朝大海,台下的观众却稀疏寥落,多是白发萧疏的老者。电子屏幕映着流动的山水背景,一个年轻的雷剧团正上演新编的《杨门女将》。那扮演穆桂英的姑娘,眼神清亮,唱腔里迸发着青春的血性与无畏的担当。
幕间休息,我悄然绕至后台,昏黄的灯光下,几位年轻演员正在整理繁复的戏服。攀谈起来,才知他们多来自雷剧专业的学校,怀揣着对这门古老艺术近乎固执的热爱,甘愿忍受清贫与奔波。
我重新坐回台下,望着台上翻飞的水袖与年轻的脸庞,海风依旧裹着咸腥扑面而来。刹那间,时光重叠,我仿佛又变回那个被奶奶紧攥小手、被父亲扛在肩头的海岛孩童。台上演绎的忠奸恩仇、家国大义,此刻听来字字千钧,清晰如昨。当年戏文中那些无声的教诲,早已化作奔涌在我血脉中的惊雷——它炸开过孤岛的蒙昧,照亮过异乡的迷途,最终沉淀为我立身处世不可撼动的基石。
戏近尾声,穆桂英高亢的唱腔裂石穿云,直冲霄汉,我潸然泪下。这自雷州歌谣中生长了300余年的古老剧种,其魂魄从未断绝。它曾是一代代海岛人瞭望大千世界的唯一舷窗,是道德启蒙的火种。如今,它更是穿越岁月烟尘的生命回响,在一代代年轻血脉的接力吟唱中,证明着一种源自土地深处的精神韧度。
当台上年轻的穆桂英引吭高歌,那声音仿佛穿透海岛的薄雾,与童年时奶奶的叮咛、爷爷的击节、父亲的低语汇聚成一股洪流。戏文中的忠义早已如海风蚀刻礁石,在我心头留下不可磨灭的纹路——雷剧入骨,便有了方向。
这微弱的灯火与年轻的歌声在咸腥海风里倔强摇曳,不是苟延残喘的余烬,而是劈开沉暗、生生不息的天际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