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文物局公布2024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来自广州的“‘常态化补助制度’破解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难题”获评入围案例。
早在2013年,广州先试先行,修订《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指出“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明确了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的用途范围——既包括“对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抢修的资助”,也包括“对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修缮、保养的补助”,从而逐步建立起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常态化补助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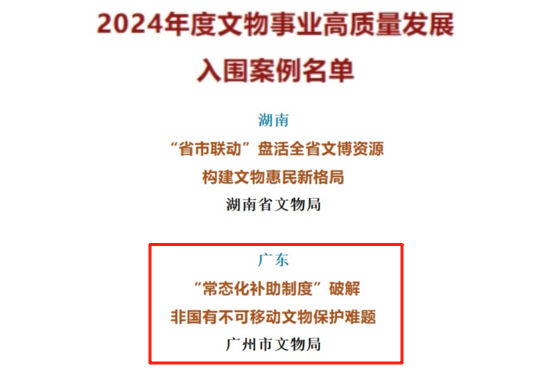
自2014年广州市正式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以来,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常态化补助制度已施行十二年。就其中甘苦、得失,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郑小炉——
广州独一份:对非国有文物进行普惠性补助
羊城晚报:广州常态化补助制度主要是针对解决文物保护过程中哪些痛点、难点?
郑小炉:广州建立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常态化补助制度,既是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现实需求,也是政策探索的主动作为。广州的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制度,尤其是针对非国有文物的专项补助,在全国范围内是起步最早的。据了解,广州也是目前全国唯一对非国有文物进行普惠性补助的城市。
随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推进,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面临的资金投入难、保护主体落实难等共性问题在全国各地都愈发凸显出来。因此,广州在文物保护之路上的探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可以给大家提供可参考、可复制的经验样本。

羊城晚报: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在广州登记文物中占比很大,它们的保护修缮工作具体面临哪些困境?
郑小炉:广州市有“三普”登记文物4533处,其中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约比占70%。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往往产权复杂、产权不清,保护管理责任人难以确定,修缮工作推进难度大。
最为典型的困境是由于历史原因导致产权分散、产权不清。比如家族共有的祠堂,还有一些民居、书院等,后代子孙散居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祠堂的保护修缮没有人牵头负责;
再比如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岗埔围垄屋,它集宗祠与民居于一体,其中祠堂归属村集体所有、民居归多户村民分别所有,修缮时“各管一段”却又“无人担责”,导致年久失修、安全隐患加剧。
另一个常见困境就是权利与义务失衡。非国有文物的产权虽然归私人或集体所有,但也具有相应的公益属性,承载着地方历史文化。在原有机制下,产权人要承担超过普通物业的修缮成本和管理义务,却缺乏相应的支持。久而久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保护意愿越来越低,甚至出现“宁愿任其破败也不愿碰”的心态。
产权复杂的问题一时间难以从政策角度突破,但政府“兜底”式的普惠性补助可以很大程度化解权利与义务失衡的困境,并且这一举措也最具时效。
在我们现行的具体补助办法中,不以文物所有人是否具备修缮能力作为补助前提,而是对所有符合条件的文物保护项目实施普惠性补助;也不再将文物保护项目是否安排配套资金作为先决条件。
这真正实现了文物保护的普惠性,化解了“私产公益”的矛盾。在这一点上,突破了文物保护领域传统和普遍的做法。

羊城晚报:广州的这项制度从创建起,到如今入围国家文物局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中间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郑小炉:广州的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常态化补助制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打怪升级”,从顶层设计到落地细节,一步步织密保护网络。
2014年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落地以后,我们紧接着在2015年2月制定了《广州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对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维修保养进行资助的流程等,为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这个办法还先后在2018年、2023年进行两次修订,不断改进完善细节。比如增加了“事后补助”的机制,鼓励产权人先依法定程序组织修缮,然后申请补助。
例如,“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宝源路5号是由私人业主所有,他自筹经费20万元开展一期修缮工程,通过验收后申请事后补助,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予以全额补助。
此外,我们还通过制定工作指引、完善申报材料要求等,强化各区对项目的审核把关力,因为他们对本区文物情况最为了解。主要从文物修缮保护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审核把关,确保政策与补助资金落实到位。
文物保护没有“等级之别”
羊城晚报: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常态化补助制度施行过程中,有哪些代表性案例?
郑小炉:2020年、2023年,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物局)先后组织举办了广州市首批和第二批文物保护利用典型案例推介活动,广州也因此成为自2019年国家文物局首次发布《文物建筑开放利用案例指南》以来,国内首个公布本地“文物保护利用典型案例”名单的城市。
例如,番禺善世堂是最早的典型案例之一,也是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中政府与社会力量有机融合的范例。它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曾因年久失修,文物本体残损严重。从2011年起,政府引导动员了镇街、村社、陈氏族人等多方力量共同推动善世堂的修缮工程。当时还有文物保护志愿者积极参与进来,其中有几位年轻人正好是陈氏后人。
再如广州东山的逵园,不仅完成了修缮,后续还得到了很好的活化利用,成为集画廊、咖啡馆和文化活动等为一体的艺术新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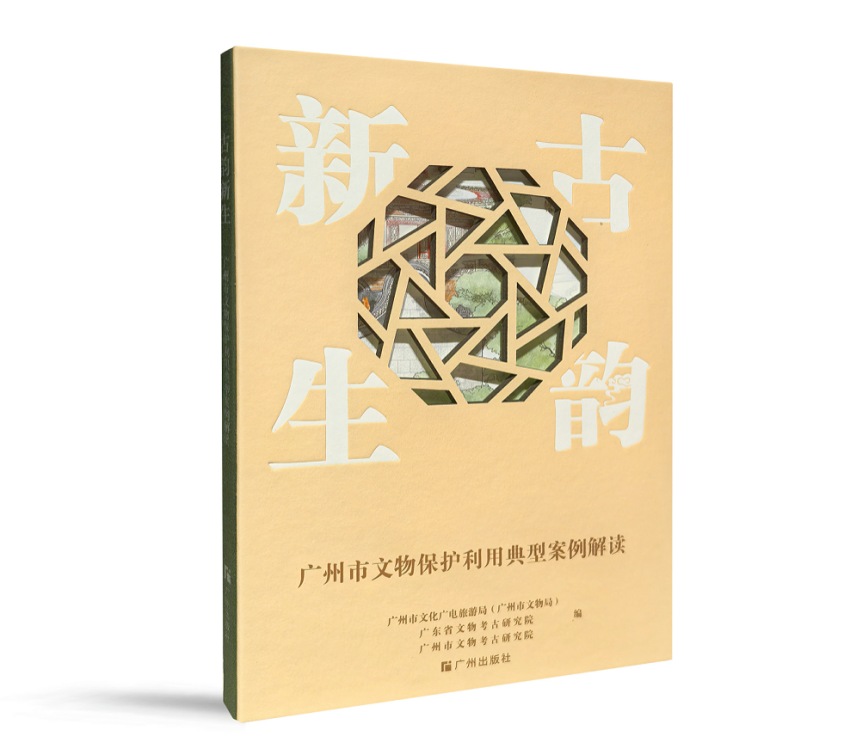
羊城晚报:在这一制度下,如何平衡财政压力与保护需求?这一制度可以在其他城市或地区复制吗?
郑小炉:常态化补助制度每五年为一个周期,2014至2018年每年预算上限6000万元,2019至2023年每年4300万元,2024至2028年每年4500万元,累计安排了5.15亿元。
这些都是不可移动文物的“救命钱”,优先保障修缮存在险情、亟需抢险排危的文物,维系文物的“生命线”,让它们得以存续。另一方面,侧重补助保养维修有活化利用计划的文物。
截至目前,广州共补助文物保护工程项目1219个,投入资金3.75亿元,其中非国有文物929个,共2.52亿元,占比67.2%。这样的投入相对全国其他城市来说也并不算少。
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专项补助并不是“大包大揽”,不是政府包办文物的保护利用,而是通过“普惠性支持+精准化引导”,让产权人觉得“保护有奔头”,让社会力量看到“参与有路径”,非常希望未来看到项目不断延续推进。
这一制度可复制性很强,设立专项资金补助其实在财政中投入占比不大,关键在于能够让濒临消失的文物得到抢救保护,最基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文物的存续,文脉的传承。
实际上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中绝大部分都是低级别文物,它们多数都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既没有高级别文保单位的政策倾斜,又缺乏稳定的保护资金,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群体,小病害往往容易拖成大问题,最终面临消失风险。但每件文物,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各级政府对本辖区内的文物都有相应的保护责任,各地只要落实这一观念就能推行。

积极迎接文物保护新挑战
羊城晚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32条有了“县级以上政府可予以补助”的条款,在获得法律保障和支撑后,未来广州的补助标准、覆盖范围等是否会有进一步调整?
郑小炉: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从国家层面推动各地政府承担起更多文物保护的责任。可以说大家的理念一致,广州的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常态化补助制度与其相呼应。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的修订,考虑完善专项资金的制度管理,并且有可能进一步拓展专项资金的补助范围,不过还需更多论证和多方征求意见。入围国家文物局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又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提供保障,该制度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
羊城晚报:对有活化利用计划的项目“倾斜补助”,在此过程中如何平衡“保护”与“商业化”边界?
郑小炉:这一问题很早便考虑到了,2013年修订《规定》时明确给出了限制性条款:“禁止对文物进行破坏性利用。禁止从事可能危及文物安全的活动。利用不可移动文物的,不得破坏文物历史风貌及周边环境......”
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支持并鼓励文物的活化利用,前提便是保障文物安全、不衰减文物价值。文物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通过常态化补助制度修缮保护文物只是第一步。
比如宗祠的修缮往往会发挥意想不到的示范作用,一个宗祠修缮保护好之后,十里八乡的村民群众都会学习借鉴,自发地回到各自村子推动本村的不可移动文物修缮保护。这个过程中所建立起的公众认同感与积极性,比政府“大包大揽”要重要得多。
文、视频 | 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
图|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