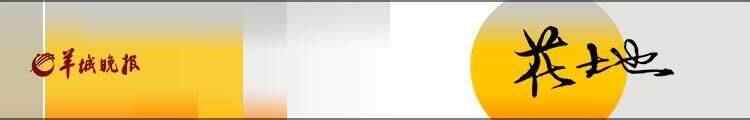
文/邵文杰
北京的初秋,天色澄净如一方新砚,蓄着极淡的玉色。风自西北来,掠过鼓楼檐角,铁马轻撞,缺一拍,恍若母亲信末的省略号。
什刹海北岸,我执竹丝胎油纸伞,伞面柿漆书“无远弗届”,行楷温厚,墨中掺了夜合花汁,甜意极轻,似一句未出口的低唤。伞柄虽藏发热丝,却未撑开,今日无晴无雨,只任初秋的光斜照,将人影叠作新裱绢本,旧墨未干,又染微凉。
母亲不在身边。癸卯年腊月廿六,河南淮阳老宅的七株桂花落尽最后一粒金屑,她便在那阵香中安详阖眼,无疾而终,享寿九十二。
临终前日,犹伏案誊抄《古文观止》,笔驻《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之“尽”字末捺,轻轻挑出,似为我留下半瓣未写完的花。那日薄暮,我独自拭净她的书案,砚中墨痕未干,如一泓不肯结冰的湖水。将狼毫插回笔筒,笔杆上浅浅牙印,是她年少时咬下的痕。
一
暮色垂落,鼓楼如埋藏七百载的花雕,坛身覆满尘灰,却掩不住内里愈醇的香。我拾级而上,指尖掠过砖缝间一茎紫花地丁,花瓣微卷,沾露,犹含旧年雨意。
母亲生于淮阳龙湖之滨,一生未远行。壬申年初秋,我初携她来京。此后三十一年,她随我居于东城小院,将故园桂香糅入京华秋风。去年忽念淮阳,言金桂丹桂候她点香,执意南归。我留下小院一撮土,替她守着皇城的风。
风又从西北来,掠过钟楼檐角,铁马轻撞,缺一拍。屏息,以指腹轻触栏杆,恍若触及母亲腕上旧表罗马字盘,缺了秒针,是我初领薪俸为她所购。表盘映出鼓楼脊兽的剪影,似将三十一年折叠入一滴水。
我低哼《忆故人》,缺的那一拍,由记忆悄然补全。楼檐下,一只迟归的灰鸽敛翅,栖于鼓沿,如一枚迟到的音符,振羽掠过耳廓,衔走了那声未响的鼓点。
故宫西北角楼在夕照中浮起铜绿,檐角悬一枚银杏,叶未全黄,边沿已透一线赭金,如旧时宫绢上裁下的残卷。我欲伸手,忽记母亲言:“让它在风里再飞一回。”
她少时在淮阳老宅,每至深秋,总携布囊拾银杏,焙干研末,和以龙湖初雪,封坛三载,方得“秋酿”。启封之日,香透四邻。去岁此时,她信中说:“坛已空,树还在,你替我拾一枚,埋于什刹海老柳根下。”
风过,那叶在铜色檐角轻轻一颤,似敛羽的蝶。遂俯身拾起阶前一叶,叶柄犹存余温,若母亲掌心最后一点暖。我将它纳入袖中,如藏一封未启的信。角楼下御河水缓流,水面浮着几片碎金,似谁失手打翻了旧妆奁。蹲身,指尖探入水中,凉意顺指而上,如母亲为我系扣时,冰凉的指尖轻触颈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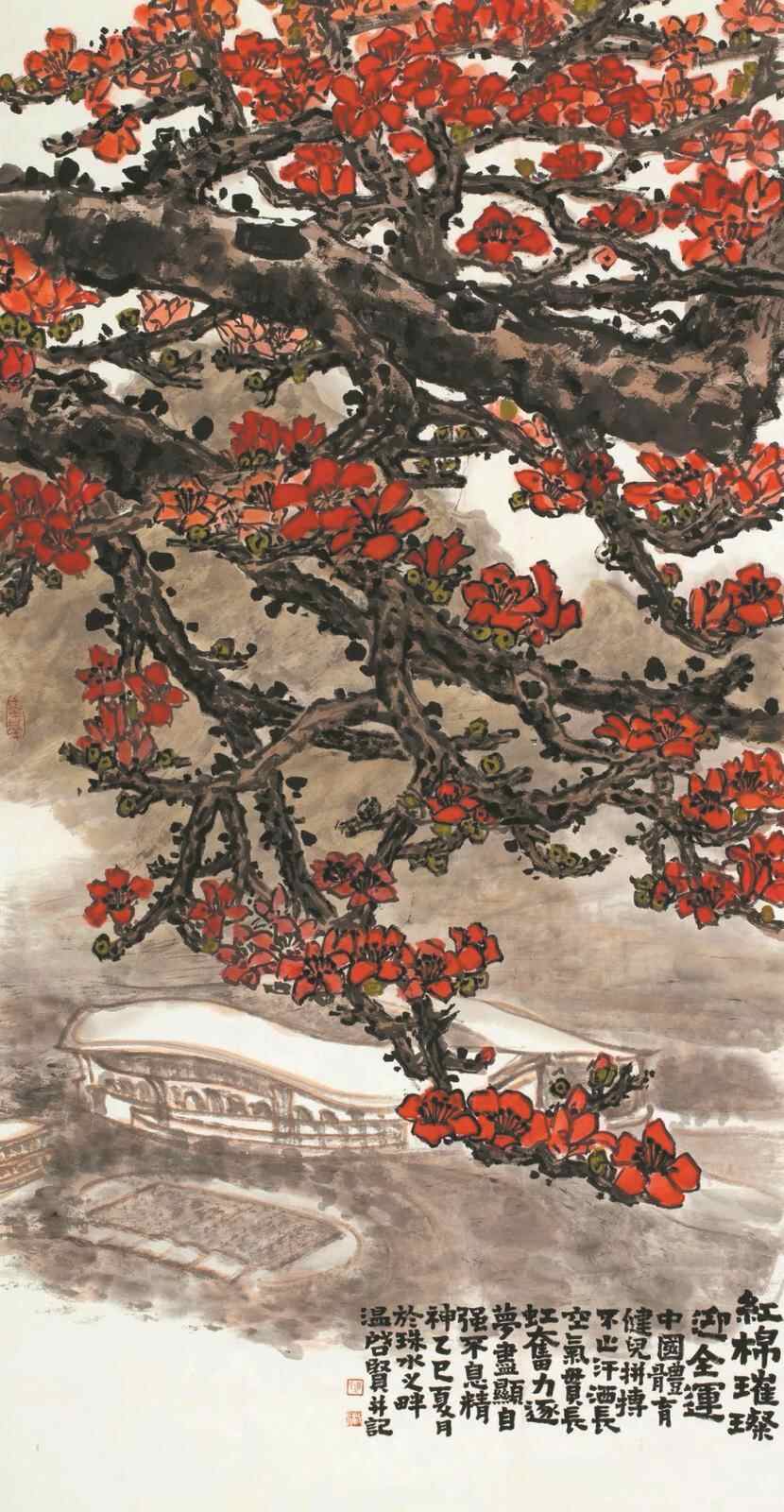
二
后海的夜色掺了桂香,却非真桂,是母亲旧年寄来的干花——淮阳丹桂与金桂,三蒸三晒,蜜渍封于白瓷罐。罐身题“花酿”二字,行楷温厚,乃母亲手迹。
循香至银锭桥畔,见一舟自横。舟尾立一少女,月白立领衫,腰束绛绡,手执青篙,篙尖点水,如蜻蜓剪浪。舟首乌篷小炉煨着砂铫,粥香如雾。
少女隔舟轻唤:“邵先生?老夫人前年嘱我温粥,三分苦,七分甘。”声清婉,带晨起磨豆浆的微哑。我颔首,未取粥,只道:“替我谢过厨下,老齿畏甜,留一分龙湖水便好。”
粥香袅袅,与后海夜色交融,竟似母亲当年手植的老桂,在风中轻轻翻动枝叶。少女听罢,垂篙一点,小舟离岸尺许。背影渐融于灯影,如一幅被水洇湿的工笔,唯余那点绛绡,在雾中晃成朱砂。
胡同老柳的枝条似内嵌温感丝,遇寒自绿,遇暖转黄。折下一缕,绕指成环,忆母亲语:“柳可再绿,人难再少。远行带着它,就当带着淮阳。”
旧居院门半掩,铜环已绿。推门,海棠犹在,花期已过,枝头悬几粒红果,如未写完的诗行。触那果实,指尖沾一层薄霜粉,凉意极轻。母亲旧居窗下,曾有一口花砖小井,沿生青苔。
她在京的三十一年里,常临井梳辫,辫梢桂瓣随水波轻漾。今井已封,苔痕愈厚。将柳环轻置井盖上,似替母亲将最后一缕青丝归还尘土。苔痕间,一只蜗牛缓缓爬行,留下银亮的迹,如母亲少时银簪划过发间的光。蹲身看它一寸寸爬过“花酿”罐底,似在替我丈量淮阳至京华的路。
三
北海的月色是旧的,像母亲腕上旧表的玻璃,凝着一弯月痕。立于琼华岛下,看白塔倒影被风揉碎,复又聚拢。
母亲曾说,北京的月华比别处亮,因皇城根下的尘土重,月光落下,便沾了金粉。仰首,果见月色中浮游着极细的尘,如壬申年我初携她夜游北海时,窗棂上闪烁的金箔,明明灭灭,不肯沉坠。
取出母亲旧年寄来的芦管,掐去顶端,中空如笛,却吹不成调。只嘘出一缕白絮,随风飘向白塔,若一封无字的信。信中写着:母亲,我替你拾了银杏,埋在老柳根下;替你听了角楼风铃,缺的那一拍,用记忆补全;替你尝了桂花粥,苦中带甘,正如此刻;替你折了柳环,带着它,就如带着淮阳。塔顶铜铃忽轻响一声,似替我签收。
夜深,归东城小舍。窗台上,白瓷“花酿”罐仍满,封蜡完好。母亲去后,我再不忍启封。
将银杏叶夹入《古文观止》扉页,柳环悬于书架显眼处,芦管插入青瓷瓶,瓶底铺着淮阳旧土。熄灯时,芦管竟透出一点微绿,似母亲当年夹入书中的最后一瓣桂。
风过窗隙,携来远方的钟声,非鼓楼,非角楼,是淮阳龙湖太昊陵古柏间,母亲将最后一笔化作了风。
风过淮阳,风过北京,风过三十一年的光阴,终落于耳畔,轻轻一句:“我在呢,别怕。”
抚过瓷罐,蜡封沁凉,指尖却留一缕隐约的暖。那是母亲用九十一个秋天淬炼的一瓣香魂,如今在我掌心,无声地醒成了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