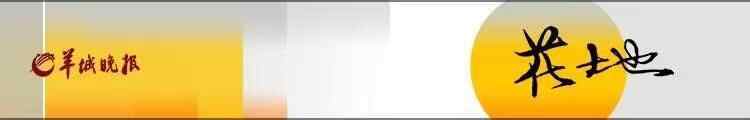
文/钟哲平
广州华侨新村友爱路20号,有一座红顶白墙的小洋楼。花园里桂花飘香,池中游鱼嬉戏,白兰花树影婆娑,掩映着一尊优美的塑像。
这里是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的旧居。1955年,红线女怀着对广阔艺术天地的向往,从香港回到内地,投身新时代文艺事业,就一直在这里生活、工作、课徒。
在红线女离去12年后,这里依然陈列着红线女的代表作品、起居摆设、道具戏服,以及她为粤剧奉献一生的点滴痕迹。小洋楼内不时举办各种粤剧沙龙,悠扬粤韵,绕梁往复。今年是红线女诞辰一百周年,红线女旧居还推出了“《刁蛮公主戆驸马》主题展”“解锁红线女同款Citywalk”等活动。城中有不少粤剧文化传承传播基地,而友爱路20号却不同于一般的博物馆,这是一个有历史、有回忆、有人情味的地方。
不久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在红线女旧居取景。笔者作为该记录工程的学术专员,与红线女大弟子欧凯明进行了深入访谈。
以下文字,是欧凯明断断续续的讲述。“只道真情易写,那知怨句难工”,情到深处,回忆是琐碎而闪光的。其中有简单生活中的幸福感,有对艺术与知识的饥饿感,也有在洪流中坚持自己的选择、在名利中呵护心智的单纯。

1
1989年,我在南宁粤剧团工作。那时粤剧低迷,无戏可做。我每月工资64元,加上困难补助也就98元,吃饭都不够。为了补贴生计,我们就去歌舞厅兼职唱歌。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拍电视剧。我参演过《远征》《百色起义》等剧目。我在剧组等拍摄的时候,常常在草地上练功,踢腿、走旋子、翻跟斗……导演说:“你一身功夫,能打能唱,干脆到制片厂来吧。”我有点心动,但又不舍得粤剧舞台。我们戏曲演员都讲童子功,我13岁开始学做戏,打一年哭一年练几年,才掌握一点基本功,实在不舍得放弃。传统戏曲是令人着迷的,拍电影时,镜头可以不断重复,拍到导演满意为止。但戏曲舞台就不一样了,锣鼓一响,角儿就入戏,一鼓作气演到落幕,很过瘾的。
理想难以为继,何去何从?当我最彷徨、最无助的时候,我的恩师红线女出现了。
有一天,南宁市文研所的所长对我说:“喜事啊,女姐睇啱你了!”原来所长收到了粤剧演员李飞龙的电报,李飞龙受红线女委托,要来南宁考察我的功底。
我后来才知道,1991年中秋节,我在南宁电视台举办的晚会上演折子戏《吴刚捧出桂花酒》,当晚著名相声演员黄俊英也同台演出。黄俊英老师回广州后,对红线女说:“广西有个后生仔叫欧小胡(我的原名),声音和基本功很好,形象也不错。你若要物色粤剧人才,不妨找人去看看。”
李飞龙见过我之后,就打电话给红线女说:“这个年轻人的确不错,可以培养。不过跨省调动难度很大,你要亲自出马,别人搞不掂!”
在红老师的努力下,我的工作调动提上了日程。1991年底,李飞龙就安排我到广州“过堂”。“过堂”地点就在红线女老师家中。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位文化局、粤剧团的领导。红老师叫我唱一句,我就唱了一句首板。她说:“几好啊,你把声比录像里面仲好听。”红老师叫我踢一下腿,看看基本功。又问我会不会翻筋斗。我说客厅里面只能翻小翻,就到室外翻了一下。
看得出红老师对我比较满意。她说:“大家对你印象不错,你对调动过来有什么要求呢?”我说:“有床睡、有地方练功、有戏演,就可以了。只有一件事,我老家有个女朋友叫蒙菁,和我同班学粤剧的。如果我自己离开南宁,人家会说我是陈世美。能不能把她一起调过来?就算她调过来以后不嫁我也没关系。”
红老师笑笑,没出声。后来我听那天在场的人说,我离开华侨新村后,红老师就对旁人说:“哈哈,这个臭小子挺有良心的。”
红老师果然把我和蒙菁一起调过来了。蒙菁后来成了我的太太。
2
我初来广州时,就在红老师家住过半年。当时黎骏声、苏春梅、余楚杏也住在这里。余楚杏和黎骏声住三楼,我和苏春梅住一楼。我们每天晨起练功,然后去桂花岗广州粤剧院排戏,下班回来吃饭。
那时我年轻力壮,练功消耗又大,饭量很大,一顿饭要吃半斤米才够饱。红老师不收我们伙食费,但我主动提出每个月要交200元。我说:“老师,如果唔交钱,我唔好意思装饭,食不饱。”红老师说:“啊!你未吃饱啊?你无装饭咩?”我说:“装是装了两碗,不过你家的碗小,我要食五碗才够饱。”红老师笑了笑说,你们工资不多,就交150元算了。后来她还是不收,吩咐我安心吃、敞开吃。红老师还交代煮饭阿姨尽量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每餐都要有肉有汤。
我们这几个学生,能够跟随红老师学习,实在是很幸运的。红老师是我们的“严师慈母”。红老师对待艺术非常严肃,她在家时,我们多少都有点紧张,不敢多说话。如果红老师有演出,她提前三天就开始封声,不和我们说话。到点吃饭了,就拍几下手掌,我们就下来吃饭,吃饭的时候也是不说话的。
后来我为了工作方便,搬到桂花岗粤剧院宿舍住,不久后就成家了。我的儿子欧豪和红老师很亲,也在红老师家住过两三年。红老师教欧豪读书写字,欧豪一直叫她红奶奶。
回忆起红老师的身教言传,最难忘的还是她对艺术的执着。红老师把粤剧视为生命,每创造一个人物、设计一句唱腔,都用生命去拥抱这种艺术。我去看她排演粤剧《祥林嫂》时,目睹她全身心投入,很受感动。红老师以往饰演的舞台形象都是靓丽的,而当她化身为祥林嫂,是那么凄苦、那么悲愤,她用饱满的情感、跌宕的唱腔、极具张力的身段,去演绎一个悲情人物、控诉一个封建时代。
红老师教我们做戏,是因材施教的。对郭凤女、黎骏声、苏春梅和对我的要求,都不一样。她会结合我们自身的唱腔特色来指导我们。比如我学习马派(马师曾)唱腔时,红老师叫我不要“学得太像”,因为马派的发音方式会对声带有影响。但如果唱不出马派的声音质感,观众又很难认可。红老师就教我,少模仿声音,多模仿节奏。后来我每次演《审死官》《关汉卿》《搜书院》等马派名剧,观众都掌声如雷。可见大家很怀念马大哥。
红老师对每一部戏、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她来看我们排练《刑场上的婚礼》,看得很投入,要亲自演唱高潮部分的幕后伴唱。我们递给她一个麦,她立即就在排练场唱了起来。这个录音我们一直保留着,后来《刑场上的婚礼》拍成电影,就使用了红老师的原唱。红老师去世以后,我们每次演这个戏,演到这一段,就不禁热泪盈眶,我们很难接受,红老师真的走了。
访谈结束时,我们坐在旧居小院子的木桩凳上聊天,一抹斜阳照在高高的菠萝蜜大树上,硕果金黄。这些小凳子是用院中的白兰树修剪下来的树干制成的。院中的白兰、菠萝蜜、凤眼果、含笑花、佛肚竹等老树,都是红线女刚住进来时亲手种下的。如今花香、果香、枝叶、树干,依然福荫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