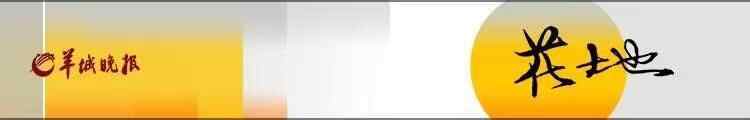
文/唐秋娴 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2025级中文16班
品读南翔先生的《梅岭古道踏春来》,起初以为是一篇普通的踏春游记,却在温润如春雨般的文字中慢慢感受到千年历史在梅岭古道中的沉淀。跟随着作者的步伐,我在文字中体会到,这场踏春不仅是寻访,更是一场与山河历史的对话。
作者开头用南昌的梅岭引出惦念25年之久的位于赣粤交界的梅岭,将自然景致、历史遗迹和人文记忆编制成篇。
寒风细雨中,作者踏上了梅岭古道,以“梅”为钥匙,打开了这次踏春之旅。与古人所写的梅花不同,作者笔下梅岭道边的梅花带着几分参差的生动:最早开放的梅花已花谢生叶,枝头的绿色“如万千落在枝头的粉蝶”,而有的才刚刚开放,“红白含羞,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当地友人说“赏梅的时节依天气而定,天寒则花盛”,让春景更加真实可感。
若美景是梅岭古道的衣袂,细品历史便更见其风骨。先生每迈出一步,都能叩响一段过往。道旁那棵1400岁的“江西枫香树王”,四五人方能合围的树干、如巨石般暴露的根茎,与周围后生小辈的树丛形成强烈对比。这棵“老而弥坚”的古树,恰是古道兴衰的见证者,让人耳畔仿佛响起“千余年前车马呼哧呼哧的气喘声、挑夫汗落如雨的噼啪声”。
脚下的碎石路更藏着光阴的密码:那些“似圆非圆的坑道”里,圆形的马蹄印与椭圆形的拐锥孔,以物态的方式记载着2000年的商旅繁华。作者将其比作“反复皴擦的水墨”,无数人的足迹叠加在碎石之上,便晕染出跨越千年的历史长卷。

梅关之巅,是历史与地理的双重坐标。这座建于明成化十五年的关楼,虽上层已塌,仅存的关门仍透着气势。门楣上“南粤雄关”与“岭南第一关”的匾额,默默划分着赣粤两省的疆域,也见证着它曾兼具军事防御与关税征收功能的历史。
史载,清嘉庆年间,大庾岭商道课税远超武昌关,又让这“岭南第一关”多了层“最早海关”的厚重。“大庾岭”之名的由来更藏着巧合:既因汉代庾胜将军在此屯兵传播文化,又因山形似“禀庾”契合《诗经》“我庾维亿”的意象。自然与人文的缘分在此悄然交织。
最令人动容的,是古道上古今的呼应与传承。作者此行,本就带着跨越25年的牵挂——从南昌到深圳,地理的迁徙从未消解他对梅岭的惦念。这种牵挂恰与古道承载的文化基因相呼应:这里曾走过“不趁青梅尝煮酒”的苏轼,走过“岭色随行棹”的汤显祖,也走过主持开凿驿道的张九龄……无数文人墨客的足迹让古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古诗之路”。
下山时,作者偶遇舞龙迎春队伍,恰让历史与当下完成了温暖对接:锣鼓声中翩跹飘落的梅花,既是春的信号,也是古道生命力的延续。正如那些每年新种的梅树,虽非古木,却在延续着梅岭的风骨;而守道人日复一日的日常维护,也让千年驿道保持着温度。
作者笔下的梅岭古道愈发清晰:它是张九龄凿山开路的远见,是苏轼南迁北归的感慨,是枫香树历经千年的坚守,更是春日里花瓣与锣鼓共舞的生机。这条连接赣粤的古道,早已超越了交通要道原本的意义,成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线,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纽带。
作者“踏春”,赏的是文化根脉。那些看似细碎的发现——枫香与枫树的区别、马蹄印的成因、“庾”字的渊源,都是与历史对话的密码。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这样的行走与书写让我更觉珍贵:它提醒我们,每一条古道都藏着山河记忆,每一次驻足都能听见历史回声。当春风再拂梅岭,新花会开,新的足迹也会踏上碎石路,而古道承载的文明与精神,终将在这样的古今对话中保持着鲜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