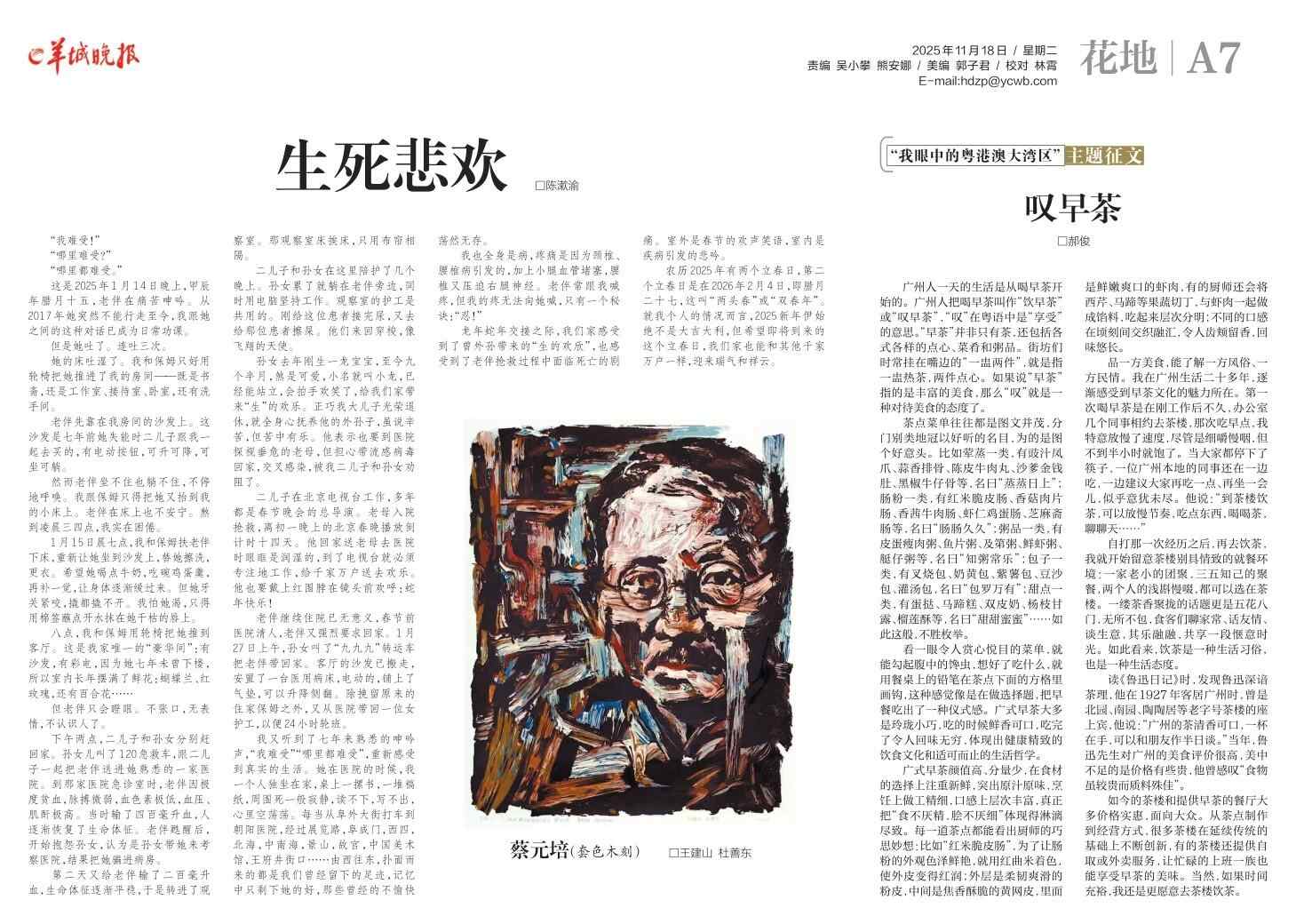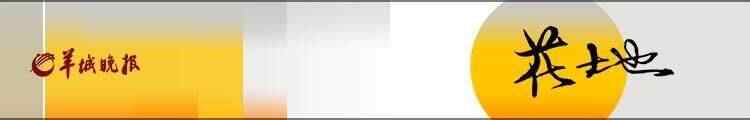
文/郝俊
广州人一天的生活是从喝早茶开始的。广州人把喝早茶叫作“饮早茶”或“叹早茶”,“叹”在粤语中是“享受”的意思。“早茶”并非只有茶,还包括各式各样的点心、菜肴和粥品。街坊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盅两件”,就是指一盅热茶,两件点心。如果说“早茶”指的是丰富的美食,那么“叹”就是一种对待美食的态度了。
茶点菜单往往都是图文并茂,分门别类地冠以好听的名目,为的是图个好意头。比如荤蒸一类,有豉汁凤爪、蒜香排骨、陈皮牛肉丸、沙爹金钱肚、黑椒牛仔骨等,名曰“蒸蒸日上”;肠粉一类,有红米脆皮肠、香菇肉片肠、香茜牛肉肠、虾仁鸡蛋肠、芝麻斋肠等,名曰“肠肠久久”;粥品一类,有皮蛋瘦肉粥、鱼片粥、及第粥、鲜虾粥、艇仔粥等,名曰“知粥常乐”;包子一类,有叉烧包、奶黄包、紫薯包、豆沙包、灌汤包,名曰“包罗万有”;甜点一类,有蛋挞、马蹄糕、双皮奶、杨枝甘露、榴莲酥等,名曰“甜甜蜜蜜”……如此这般,不胜枚举。
看一眼令人赏心悦目的菜单,就能勾起腹中的馋虫,想好了吃什么,就用餐桌上的铅笔在茶点下面的方格里画钩,这种感觉像是在做选择题,把早餐吃出了一种仪式感。广式早茶大多是玲珑小巧,吃的时候鲜香可口,吃完了令人回味无穷,体现出健康精致的饮食文化和适可而止的生活哲学。

广式早茶颜值高、分量少,在食材的选择上注重新鲜,突出原汁原味,烹饪上做工精细,口感上层次丰富,真正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体现得淋漓尽致。每一道茶点都能看出厨师的巧思妙想:比如“红米脆皮肠”,为了让肠粉的外观色泽鲜艳,就用红曲米着色,使外皮变得红润;外层是柔韧爽滑的粉皮,中间是焦香酥脆的黄网皮,里面是鲜嫩爽口的虾肉,有的厨师还会将西芹、马蹄等果蔬切丁,与虾肉一起做成馅料,吃起来层次分明;不同的口感在顷刻间交织融汇,令人齿颊留香,回味悠长。
品一方美食,能了解一方风俗、一方民情。我在广州生活二十多年,逐渐感受到早茶文化的魅力所在。第一次喝早茶是在刚工作后不久,办公室几个同事相约去茶楼,那次吃早点,我特意放慢了速度,尽管是细嚼慢咽,但不到半小时就饱了。当大家都停下了筷子,一位广州本地的同事还在一边吃,一边建议大家再吃一点、再坐一会儿,似乎意犹未尽。他说:“到茶楼饮茶,可以放慢节奏,吃点东西,喝喝茶,聊聊天……”
自打那一次经历之后,再去饮茶,我就开始留意茶楼别具情致的就餐环境:一家老小的团聚,三五知己的聚餐,两个人的浅斟慢啜,都可以选在茶楼。一缕茶香聚拢的话题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食客们聊家常、话友情、谈生意,其乐融融,共享一段惬意时光。如此看来,饮茶是一种生活习俗,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读《鲁迅日记》时,发现鲁迅深谙茶理,他在1927年客居广州时,曾是北园、南园、陶陶居等老字号茶楼的座上宾,他说:“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当年,鲁迅先生对广州的美食评价很高,美中不足的是价格有些贵,他曾感叹“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
如今的茶楼和提供早茶的餐厅大多价格实惠,面向大众。从茶点制作到经营方式,很多茶楼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有的茶楼还提供自取或外卖服务,让忙碌的上班一族也能享受早茶的美味。当然,如果时间充裕,我还是更愿意去茶楼饮茶。
——“我眼中的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征文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