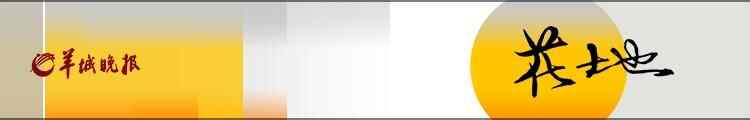
文/李远芳
在粤东客家地区,许多人是听着睡前童话“老虎外婆”长大的——童话里,两姊妹要去外婆家,越过山岗时,一只老虎蹦了出来,谎称是她们的外婆。姐姐说:你不是,外婆是“着青衫”的。老虎扯下几片芭蕉叶,裹在身上说:看啊,外婆的青衫……
我向来很喜欢这个情节,每次听阿嬷讲到这里,都要想象一下芭蕉青衫的样子。我总以为,如此富有岭南色彩的童话就该画成图书,让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阅读。后来听说,惠阳、东莞、深圳一带客家人的民间故事里,也有这个情节,只是“老虎姐婆(外婆)”换成了“熊家嫲”,也就是母熊。且姐姐口中的“青衫”,换成了“绸布衫”。“绸布衫”似乎更加贴切,而且它和芭蕉叶一样,都是滑溜溜的。但还是觉得“青衫”更为形象、直观。
一提到“芭蕉青衫”,我就会想起家乡那一大片的蕉园。我家并不种蕉,但自打有记忆起,家里隔三岔五就会出现一串芭蕉,它们是母亲从老家或郊外亲戚家运回来的。这种自家种的芭蕉果实,是不香的,我们自然不叫它香蕉。在惠州、龙岗等地,人们都叫它“牙蕉”;在梅县、潮汕等地,人们叫它“弓蕉”。牙蕉、弓蕉,都是以形态命名的:弯曲的芭蕉,就像一个獠牙,又像一把弓。
至于量词,我们也不叫一串蕉,而是叫“一托蕉”或“一梳蕉”。因为一只手托起来的芭蕉的量,就是“一托”;而一根根芭蕉如梳齿般稠密有序地排列着,就形成“一梳”。
我总觉得似乎某样事物在一个地方越是常见,那个地方与它相关的词汇就会表达得越精准。比如游牧民族的语言中,与马有关的词汇往往很丰富;在寒冷地带,与雪有关的词汇往往也特别多;而芭蕉常见于华南,在我们方言里,牙蕉、弓蕉就比香蕉要形象,一托蕉、一梳蕉也比一串蕉更生动、形象。

这些土里土气的芭蕉非但没有香气,表面还布满了黑色斑点。年少的我是不太爱吃它的,只垂涎于市场里的香蕉。市场里的香蕉表皮鲜艳、光滑,果肉也散发出诱人香气,吃过它们,谁还看得上家里的那一梳土蕉呢?因此,每次去水果店里,我都要去挑选香蕉。
有一日,为了去探望生病的亲戚,我又跟着母亲来到水果店,正欲选香蕉,母亲一把拉住我说:“病人本身就心肝焦,你还送蕉!”我一听,哭笑不得。后来也了解到,广东许多地区都有因“蕉”“焦”谐音而不宜以蕉赠病人的说法。在民间,水果一般都被赋予了相应的果语,如橘子代表“大吉(橘)大利”,榄子代表“揽子(抱子)”,甘蔗代表“从头甜到尾”……它们都被安排在喜庆的场合里,唯独芭蕉,却是被人嫌弃的。
不过,我们怎么可能不喜欢香蕉呢,似乎为了弥补果实的遗憾,芭蕉叶倒是与喜庆日子密不可分的。过年的甜粄、清明的艾粄、冬至的萝卜粄,还有婚宴、乔迁宴中的发粄等,都由米或面做成,蒸熟后黏乎乎的,但用滑溜溜的芭蕉叶来垫着蒸,就再好不过。软糯的糕点里还会融入蕉叶的清香。要是用蒸笼纸来垫,就会少了这份岭南田园的气息。如今在一些老市场里,还可买到用蕉叶垫着蒸的早点。
但人到了一定年纪,似乎味觉就会来一场返璞归真。如今,相较于香蕉,我反而偏爱土蕉,只觉得土蕉的味道更醇厚、本真。我竟开始缠着老母亲去郊外为我寻找“牙蕉”,如从前一般,整串提着回家放熟了来吃。
以前我想不通,文人墨客为何能为芭蕉写出如此多称颂的诗词歌赋,我一直看不出这种随处可见、随手可取的植物有什么诗意。一看到诗人笔下的什么绿玉、绿蜡,我脑海里只会浮现出那些糕点下的叶片。
我总以为,只有远方的枣树、苹果树、白桦树才是美的。但随着年岁的增长,那种对远方的向往也转化为了对近处的热爱。我逐渐意识到,并非远处的陌生才是诗,童年想象中的“绸布青衫”,还有各式糕点里的蕉叶清香,和家乡方言里的牙蕉、弓蕉,一托、一梳,又何尝不美,不是诗意盎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