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永远要对莫言这样的作家抱以期待”“其实段子手、喜剧人的形象并非余华所愿”“年轻人就应该过漏洞百出、意气风发的人生”“如果你过度迷恋、追求快乐阅读,那你的阅读可能就永远在一个平面滑行,很难有真正的收获”……
近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做客羊城晚报音频节目“花地有声”,金句频出。他借由自己最近出版的新书《文学的深意》,谈及当下鲜活的文学现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文学时刻——

莫言一定还会写出“惊艳”的作品
羊城晚报:在您的新书《文学的深意》里,点评了很多作家作品,像莫言的《檀香刑》、于坚的散文、李洱的《应物兄》、东西的《回响》等。作为一个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您和很多作家都是好朋友?
谢有顺:我和作家的交往很多,跟他们有广泛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能理解为一种庸俗的关系。在我看来,批评家跟作家的交往,首先是人与人的交往。跟一个人交往,肯定要聊得来、趣味相投,这个交往的价值往往超过了专业层面的往来,并非一定要给对方写评论,没这么庸俗。我的很多作家朋友,我从来没给他写过评论,但是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羊城晚报: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大家都非常期待他能破除“诺贝尔文学奖”的魔咒,写出比《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檀香刑》更好的作品,您觉得可能吗?
谢有顺:我们永远要对莫言这样的作家抱以期待,他本就不是一个按照常规路径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都在不断突破写作常规、突破固有文学秩序。“诺奖”的魔咒也许对很多人都存在,但对莫言来说可能会失效。一方面,他获得“诺奖”时比较年轻;另一方面,他的身上有一种野生的、蓬勃的生命力,一种泥沙俱下、挣脱一切束缚的狂放力量。这种力量尽管在他现在的写作中有所收敛,但莫言的写作始终有自我的深思和变革。等着吧,他一定还会有令我们惊艳的作品。
注视无法被科学量化的瞬间
羊城晚报:现在大家大多是通过综艺节目、短视频等形式认识莫言、余华,这种现代媒体的呈现仿佛离作家很近,但又好像离作品很远。对于这种反差,您怎么看?
谢有顺:新媒体帮助塑造了两位作家的公众影响力。他们幽默、健谈,擅长用年轻人喜欢的语言来表达和描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不过余华之前跟我提到,这种媒体塑造的形象其实“非他所愿”,尽管传播力增加了,但是他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单一的“段子手”“喜剧人”这样的形象。
我能理解。毕竟他们的才华、见识和思想深度远非这么一个小片段能够涵盖的。但是两位作家对待网络与媒体没有拒斥,他们试图去理解年轻人,并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亲近年轻朋友们,这是非常好的心态。这种心态会保证一个作家走得更远。
羊城晚报:在新媒体时代,作家与读者的互动增多会对文学现场、作家写作产生影响吗?
谢有顺:不影响是不可能的,但作家在变化的语境中肯定要有所持守。刚才讲到余华、莫言,他们看起来和时代有一种新的交往方式,但骨子里、写作上一定有自己一直不变的东西。变化是一个客观事实,这种影响有时也是积极的,我们不需要过度去焦虑、抗拒。
很多人焦虑AI会取代写作,我觉得这种焦虑也为时过早。人工智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永远都不可能取代苏轼写诗,取代曹雪芹写《红楼梦》,取代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我们不用过度夸大这种变化带给人的消极影响,也要认识到它的积极方面。比如新媒体时代传播方式的变化、阅读趣味的变化,未必不会为文学带来积极的改造。
羊城晚报:确实,就像您之前在文章《为不理解、不确定而写作》中也提到,科学、技术都是试图让这个世界变得可以理解,把一切都变得确定无疑,但是文学告诉我们,世界还有许多不确定和不可理解的方面,自我也像是一个永远不能穷尽的黑洞。
谢有顺:科技和人文是相得益彰的,但也有冲突。冲突带来精神的张力。科学追求数字、准确、客观,这恰恰是文学要反抗的东西。科技越发达,越需要文学。文学告诉我们,人生和世界里还有很多不客观、不准确,在暧昧不清处、在边缘处甚至在黑暗里的东西,正等待被照亮。探索人幽深的内心世界,永远是有价值的。那些注视内心的瞬间,直击事物本质的力量,它们无法被科学量化,却是人生中非常珍贵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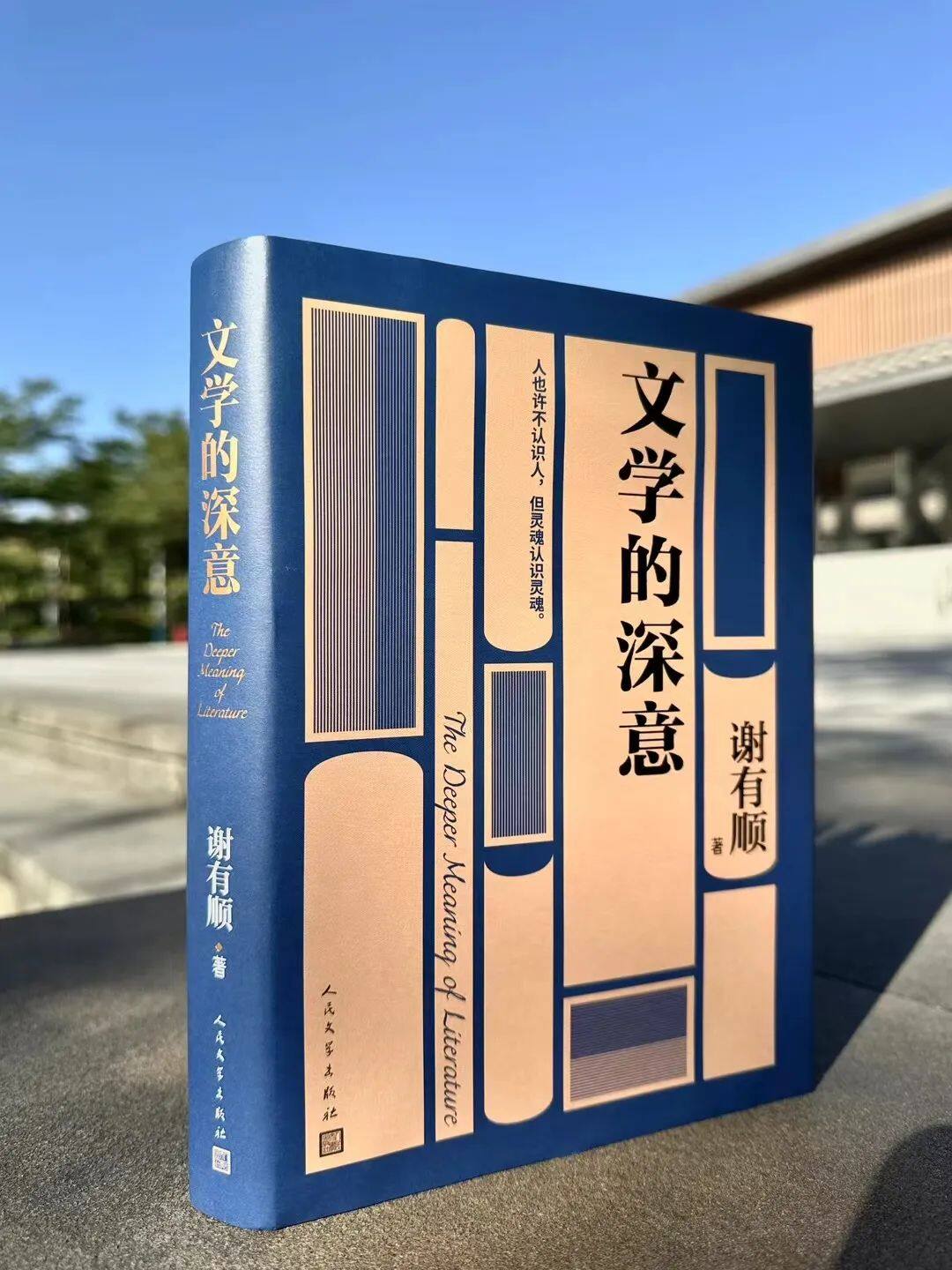
20世纪小说的主角是“内心”
羊城晚报:豆瓣上有一个热门词条叫“文学的时刻”,人们在词条下分享生活中遇到的小片段,或阅读中产生共鸣的一段话。这段话,成为他们生命中重要的文学时刻,给予了他们文学的滋养。您怎么看待这种“文学的时刻”?
谢有顺:我很向往你说的这样一个空间。其实一个人的生命丰不丰富、绵长不绵长,就是看他的人生中的这种时刻和瞬间够不够多。事实上,人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无意义中流失,你最后能回忆起来的,往往就是那一些珍贵的时刻和瞬间。
也许做很多千篇一律、无意义的事情,就是为了迎接那个即将到来的有意义的时刻,比如一个孩子的诞生,书页间解开多年困惑的一句话,等等。文学,其实就是记录和放大这些时刻和瞬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布满这种时刻和瞬间,绽放着灵光闪烁的东西。如果一部作品没有一个瞬间、一个细节能让你记住,那就谈不上是好作品。
羊城晚报: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这种文学的时刻似乎太少了。我们疲于工作,所以向往“诗和远方”。在您看来,年轻人为什么会追求“远方”?文学能不能成为这种情怀的“代餐品”?
谢有顺:年轻人要对自己好一点,要预留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你说的旅行是向外寻找,但并非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条件。除了向外寻找,我们一定要记得向内寻找。向外是一个广阔的远方,向内也是一个幽深的宇宙。年轻人大可以去放肆追求喧哗与热闹,去过漏洞百出却一往无前的人生。
当向外寻找无法满足你的时候,“行到水穷处”之余,我们还能“坐看云起时”,内心有一个更伟大而幽深的宇宙在等待着你去探索。有人曾说过,20世纪的小说如果有一个主角的话,这个主角的名字叫作内心。从文学的发展来看,从巴尔扎克到卡夫卡,文学就已经历从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向探求幽深的内心世界的转变。
羊城晚报:您刚刚提到,年轻人就应该冲动肆意。大家对您的评价都是天才早慧,您有没有过特别少年意气的一面?
谢有顺:我肯定不是什么天才,更没有什么早慧,完全是被生活的锤炼和毒打卷着走。我是一个70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辍学一年多,最后只能在村里办的中学读书。上了大学以后,不论是阅读还是其他方面,我的知识都远不如其他同学。但是我没有荒废大学时光,迅速补上功课,开始写文章。那时家里贫困,我就试着赚稿费补贴生活。靠着赚稿费读大学,这个动力也很真实,我认为它并不比“我要成为一个文学家”庸俗,甚至更具有激励人心的力量。
“我真实地介入过当下的文学”
羊城晚报:您认为文学批评的意义是什么?
谢有顺:文学批评也许是一种速朽的文体,但我至少告诉自己,我真实地介入过当下的文学,我了解当代文学的变化,我懂得一个作家是如何成长的。敢于说出谁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这是同时代批评家应有的见识和胆识。文学批评参与了当代文学的进程,即使50年后再来写文学史,依然还要参照我们这些批评家所做过的工作,没有同时代人的解读,就没有历史的积累。
羊城晚报:作为知名的文学批评家,您认为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发现一部作品里的“好”?
谢有顺:其实就是一个读书方法的问题。横扫一切的否定是很容易的,因为你对一个宏大命题作出否定判断,不用提供真实的证据。你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很容易,但你能说《透明的红萝卜》《活着》《人面桃花》是“垃圾”吗?这些是公认的好作品。有些人喜欢下一个很宏大的判断,以表现自己敢于批判的姿态,但这种判断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旦还原到具体的个案上就会显得十分可笑。
所以我说,肯定中国当代文学也需要勇气,肯定就意味着你要去“发现”。在思想、艺术、美学上发现和确认一部作品的价值是一种能力。这种“发现”取决于我们用何种方法读书。看一本书、一个作家,首先要发现他的优点,再指出他的不足。如果我们只以寻找问题的眼光来读书,怎么会得到书的滋养?
一直在读,比你读了什么更重要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有哪些具体的线索和方法能指导我们阅读呢?
谢有顺:我一直反对快乐阅读的这种说法,如果你过度迷恋快乐阅读,那你的阅读可能永远只在一个平面滑行。真正有收获的阅读,从来都是有难度的。当你啃完一本难啃的书,读懂和读通了一本经典,你的思想和见识有可能就会上一个台阶。有观念和思想创见的书,是不可能完全做到通俗易懂的。
我们永远不能让康德、黑格尔的著述通俗易懂,因为他们的思想契合的是人类精神的“塔尖”。如果你要攀登这座精神之塔,就要倾注大量时间、精力乃至意志。人一生也许不需要读很多书,几百本里有三五十本是你常读的书,我觉得就足够应对这个复杂和艰难的世界了,但问题是我们缺少精读一本书、持续读一本书的耐心。
羊城晚报: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解读人性,我们应该读些什么书?
谢有顺:当你觉得自己无法把握的时候,那就去读经典,经过50年、100年甚至几百年大家还在谈论的那个经典。读书,是要在读书中理解书、在读书中学会读书、在读书中选择书。一直在读,比你读了什么更重要。阅读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你选择你自己喜欢、感兴趣的书开始读起,读你能理解的那部分,等你读得够多的时候,内心就成长、壮大了。这个成长过程就会教你怎么选择书,以及如何更好地阅读,这本身也是一个自我了解、自我探索、自我觉悟的过程。

文|记者 孙磊 实习生 熊安娜
图|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