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花地文学榜盛典特刊⑤
11月9日-10日,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先后在广州、深圳举行。欧阳江河《宿墨和量子男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获评年度诗歌,特发表其致敬辞、感言、专访——
【致敬辞】
作为当代诗歌“贯穿式”的诗人,欧阳江河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在场状态。诗集《宿墨与量子男孩》展示的是诗人近年来21首长短各异的代表性作品,长诗气象磅礴,短诗灵动旖旎。他将自身的阅读、思考以及诗外的生命凝炼在写作中,忧思与激愤成为这本诗集内在的火焰,历史、社会、文化、人类的处境,都在其中熔炼。他的诗歌创作异质融合,具有极强的“现代感”,大大拓展了中国诗学的叙事空间。

【感言】
诗歌于我而言,是一种降临
欧阳江河
广州是我的诗歌写作的福地,我在这儿已经获得过三次荣誉了,都跟报纸有关。我特别强调诗歌的现代性、当代性,我一直认为诗歌从本质上讲,是时代的、诗意的、有历史感的新闻,如同庞德所说,历史是永久的新闻。
我目前还是深耕诗歌领域。一般人认为诗歌是春风吹拂,是飞翔,是升华,是仰望星空,是诗与远方。对我而言,以上一切都是,又都不是。诗歌于我而言,更多是一种降临。你不知道它何时降临,以何种方式降临。这种降临不是灵感,而是一种换命一样的感觉。就好像你从古代,把杜甫、韩愈活过的、余留的命换到自己身上。我今天上午去体验宋代点茶,在品茶的过程里,就感受到这种降临。点茶的小女孩就是一个大师,她点的茶原本是给苏东坡喝的,现在给我和韩东喝了,我们或许就成了苏东坡的万分之一。
此时此刻,这种降临是以花地文学榜的方式来到我身上。花与大地的关系,树与大地的关系,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李白说,“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就是这种降临最好的呈现方式。希望更多诗人可以领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降临。
(文字整理:记者 孙磊)

【访谈】
1、诗歌、哲学、数学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您曾提到,《宿墨和量子男孩》的出版,展示了您写作的一个新的阶段。该如何理解“新的阶段”?
欧阳江河:这本诗歌集确实展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很多人觉得老作家写到后来就是一直在重复自己,但我不,我在题材、主题、写法、处理时代与个人的关系方面还一直在尝试和推进。60岁之后,我进入长诗写作阶段。在这本《宿墨和量子男孩》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长诗比较多,大概有9首。
我年轻的时候也写长诗,比如《悬棺》,但它的写作不是一项任务或者决定,它是我那时对语言神奇性的一种迷恋。现在写长诗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我决定写更多东西,把我的阅读、思考以及诗歌以外的生命全放进诗歌中来,把短诗容纳不了的,甚至一度以为诗歌容纳不了的东西容纳进来。
羊城晚报:写长诗难度很大,为何如此坚持?跟短诗相比,长诗如何定义,有何优势?
欧阳江河:现代主义的长诗写作,艾略特和庞德,是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长诗。在这之前还有荷尔德林。荷尔德林的诗其实并没有那么长,几百行,但是它的规模、它的内在形态,有一种长诗精神,是长诗的气场。
我现在把300行以上的叫做长诗,我的长诗一般在300行到700行之间。但长诗不是行数有多少的统计问题,而是构架、容量、跨度、诗学观和语言形态的问题。我想通过长诗让越来越多所谓“非诗”的东西,比如新闻、网络、科学、学术、手机语言等等入诗,把写作之外的东西拉进写作的框架中,让它们完成文本的发生学转化。
羊城晚报:长诗容量很大,而且您在里面加入了非常多“非诗”的元素,尤其是大量的数学、物理知识。如何把这些“非诗”的元素转化为诗歌语言?
欧阳江河:我近几年一直在尝试用诗歌语言处理另一种语言,比如科学语言、比如贾樟柯的电影以及他在乡下盖的一座电影院。这些话语是独立存在的、与其他话语隔开的,没有被诗歌语言大规模地转化和处理过。我写《宿墨与量子男孩》,是想尝试从整体上将科学史写入诗,将科学话语转化为诗歌话语。
诗歌的语言其实可以出现在任何事物里面,很多人认为哲学、诗歌、数学一定是排除日常的,但其实它们也可以是日常的一部分。伟大的科学家常常是从日常中的小事开始不懈的追问。诗歌也是一样,我的诗歌从具体事物落笔,但背后充满了抽离的、提取的、降临的东西,充满了比思想还要思想、比理性还要理性、比具体更为具体的东西。我对更为曲折的、更为幽隐的、叠态的当代诗意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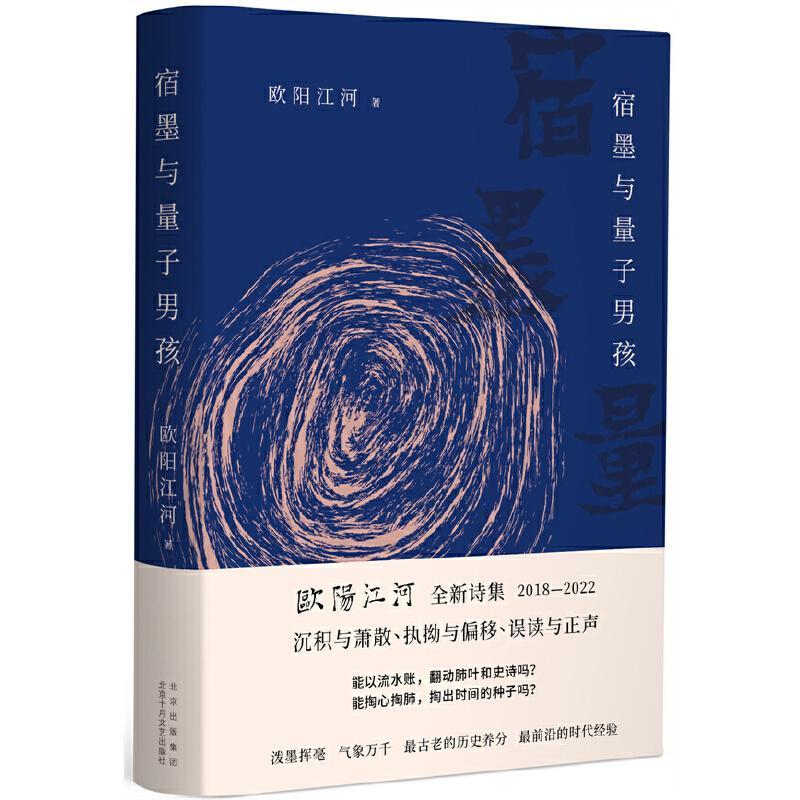
2、读者看不懂未必是作者的“原罪”
羊城晚报:您早期代表性作品《悬棺》的初衷,就是为了对自己的古代中国文学情结做一个了断,真正进入现代诗歌写作。但是在《宿墨和量子男孩》中,“宿墨”表征的书法就是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与当代性的?
欧阳江河:我现在不太使用现代性这个说法,因为现代性已经被固化为一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它是一个西方概念,它已经有了固有的时间观。我在写作的时候就发现我没有这样的时间观,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和谈论当代性。
在我看来所谓当代性就是不同时代在同一瞬间被呼魂、被激活、被浓缩,几千年前、现在此刻、以及遥远的未来,会在这个我称之为“当代”的瞬间突然呈现,我在这个时刻唤起了无数个我,唤起了万古愁,唤起了无数个世纪的各种存在。
当代性就是同时代性,是所有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以及同时代性里面的不合时宜,它永远和任何时代、任何瞬间都有点格格不入,互相抵制,互相不在对方的固有框架、限定框架里面。在这个概念深处,一个真诗人,应该无时无刻不活得如一个诗人,这不仅是一种写法问题,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状态和形态,是活法问题。
有的诗人写诗的时候才是诗人,在写诗的那一瞬间是抒情的,是感动的,是与诗意同在的,但在写诗之外他就处于跟诗歌没关系的状态之中、活法之中。我不这样,我不写诗的时候,也本能地待在诗的活状态中,不写的时候比写的时候更是一个诗人,我只是没写而已。这不仅仅是写法问题,也是活法。
羊城晚报:从古到今,从东到西,从诗的语言到数学、物理的语言,您的诗歌无比庞杂,包罗万象,会给阅读带来一定的障碍,在写的时候不担心读者看不懂吗?
欧阳江河: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我自己诗歌文本的读者。读和写一样是有分层的,这个分层不是高低贵贱之分,而是专业角度的、流量层面的大致区分,这个差异我们一定要认可。有的诗歌所有人都读得懂,我特别尊敬能把诗歌写得人人皆懂的诗人,但此一写作任务,对不起,我不认领它。我认领的是另一个写作使命,我想追求的是诗的强度、深度、难度、拓展度,寻求越来越混杂、越来越困难的一种写作方式,然后把这种写作挑战持续下去。我可能无形中对某些特定圈层的写者与读者有所冒犯。
太多人问我懂与不懂的问题。你说古代的诗歌就一定很好懂吗?屈原的诗歌有那么多的注释,很多人依然很难读懂。作家写出来的东西,读者看不懂,就一定是作者的原罪吗?我看未必。当代诗歌尚未获得像古代诗歌那样的阅读“特权”,我的意思是,当代诗从未获得让所有人都以为能看懂、但其实不懂、而又能容许这个不懂,那样一种“特权”。
当然,诗歌需要读者。但是既然我已经认领了我的诗歌之路,那我就要去承受这条道路所带来的得失与磨损,我也想我的读者越多越好,但是大流量的读者看不懂我也并不焦虑,从当下写作现场的、但也更为久远的意义上说,我这么写,是深思熟虑的,带有自己的那份决绝。
我已经认命了,一个68岁老人的写作,我不是往前走在写,而是倒过来写,写我内心深处有一些被我丢掉的或者忽略掉的存在,那些东西是真正的“原文”,我既然已经认领了写让人难懂、或者让人觉得冒犯的诗歌,那我就要对自己的这份决绝负责,同时我也要跟大流量的读者们道歉,实在对不起,我不写一读就懂的诗歌。
羊城晚报:您多次强调了作家的“60岁之后”的转折阶段,包括您自己“六十之后,我进入长诗写作阶段”,对于您而言,“60岁之后”对于作家的写作状态有着怎样的影响?
欧阳江河:我没有这样问过自己,但是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我年龄越大以后,我对有些大家都关注的、都想要得到的东西兴趣越来越少,越来越淡薄了,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里面几乎不存在了。
我对诗歌、对生命的理解越来越开阔,也越来越闭合。开阔就是能否从不同视角去看待事物和概念,闭合则是一个越来越隔离的过程,我仿佛走进一个越来越小的微观世界,变成一个粒子、一个量子、一个微生物,把整个我包容在里面。我想往那么一种生存状态,借一位古代僧侣的说法:不为致大的所拘,而为致小的所容。
3、写诗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的存在
羊城晚报:“当我身上的消极性出现的时候,我就将其转化为积极的写作。”写诗写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写不出来的消极时刻?
欧阳江河: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先说说消极性,《庚子记》就是专门处理消极性的。我迄今为止的诗歌文本中,《庚子记》是篇幅第二长的,有一千多行。
这首诗的写作主要发生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封闭在家的环境里,几乎一天写一小节,某种程度上有写日记的性质。当时我脑海里产生的假设视境是:病毒距离我只有几米远,它随时会侵入我生命,我也随时会因感染而死。这不是对可见物的直接观看,这是对“可见性”的症候式观看。
一想到死亡,所谓的消极性便立即出现了:一个人突然死了,运营商还在通知你交话费,别人还在你的朋友圈里留言,你却不能再回复,你挣的钱还没花完,你欠的钱也还没有还完,你的命还没有活够。打给你的手机铃声一直在响,你却不能接听了。这么一堆的消极性。
我问自己,如果我马上要死,作为一个诗人,我有什么遗憾,或者说有什么责任未尽?显然,我还有诗没写。所以写《庚子记》并不是积极地写作,而是在有可能染上病毒,命不久矣的预设下写的。不过我要用这种消极性,来对抗那个时期生活中的另一种消极性。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身的消极性转化为别的东西,这么一种历史的、语言形态的、包含了弱德之美、之痛的诗意转化。
羊城晚报:我非常好奇,您写诗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能有如此饱满的激情?让您一直坚持写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欧阳江河:这不是激情,不需要动力,对我来说,写诗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的本能存在。写诗是快乐的。
一个人活着总会有所回报,那就是活着本身。以前余华讲这种话的时候,我有点不以为然,现在觉得这个认知很牛。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馈赠,它把这一切称之为“惜命”,珍惜生命。生命里面原本就充满了偶然性,让我们赞美这些偶然性,让我们感恩这一切。不仅感恩美好的、也感恩不那么圆满和美好的东西。
羊城晚报:网上有文章说您被国际诗歌界称为“最好的中国诗人”,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称号的?
欧阳江河:我个人是不承认这个称号的,这个是网络的谣传,可能是哪家自媒体发布了,然后大家一看很刺激就到处转发。我不知道谁可以代表“国际”,也不知道谁能代表中国诗歌。希望借这个访谈替我辟一下谣。

4、AI取代不了人类写作
羊城晚报:您之前提到十年后会尝试写小说,这是真的吗?
欧阳江河:我肯定不会写小说。我读了太多的小说,我觉得我读就行了。
我不写小说,是想保留对写作本身的尊重,保留一个“不”的选项,实际上这是写作里面特别迷人的一点,包括我在写一首诗的时候,我永远会留出我不写的部分,这个部分,构成了这首已经写出来的诗歌里面的一个秘密,一个出口,一个绝对。
羊城晚报:可以分享一下您的日常生活吗?感觉您的朋友非常多。
欧阳江河:我的朋友很多,有的经常见面,互相插科打诨。我是川人,性格还是比较随和,不拘小节,可能冒犯了一些人,但是朋友们总的来说还是都挺厚待我的,对我比较宽容。我知道我有时候会有一点张狂,也有一些啰嗦,比如莫言老师专门为我写了首打油诗,说我别的都好,就是有点啰嗦,哈哈!写得很传神。
再比如西川,我给他写了一首有点放肆、有点疯狂的诗《西川不喝酒》,朋友们酒局小聚时从来不叫他,这个诗也成了他不喝酒的免醉牌。我很感谢这些朋友的存在,这种深远的、不觉为何的当代友谊,是多形态的、日常的、活的,没有什么功利,没有换算与换取,就是对生命的感恩和享受,就是幸福本身。活在友情中,让你觉得,当代,也是一个古代。
我自己的日常生活其实是比较枯燥的,没有既定的秩序,种种干扰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想到什么就是什么。大多数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家,对我家的猫说话,我几乎快学会说猫语了,哈哈。
羊城晚报:最后还想问一下您,在您看来这个社会还需要诗歌吗?
欧阳江河:我非常同意我的好朋友格非说的一句话,他曾经也被问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假如AI已经会写作了,那么我们还需要小说吗?格非的回答是:需要。这个回答简洁,坚定,绝对。
人只要还有肉身,还有恐惧,还有死亡,还有衰老,还有失眠症,还有失恋之类的痛苦,还有怕痛的感觉,小说、文学、诗歌就不会消失,我一点都不担心,AI取代不了人类写作的那种最根本的需要,在小说的、语言的背后构成的原文的需要,消极性的需要、降临的需要。这种幸福感、痛苦感、恐惧感,构成了文学的一个总的降临。
文学就像诗歌一样是降临,它不仅仅是写出一些我们称之为优美的句子,这些都是浅层的东西。在文学的深处,有着AI无法触碰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和诗歌永远不会消失的,人会永远需要文学。
文字访谈|记者 孙磊 实习生 黄文禹
视频文案|记者 梁善茵
图、视频拍摄|记者 宋金峪 曾育文 周巍 梁喻 刘畅
视频剪辑、包装|记者 麦宇恒 余梓涛
【2024花地文学榜】
2013年羊城晚报正式创设花地文学榜,一年一度对中国当代文坛创作进行梳理和总结,也为广大读者提供最具含金量的年度专业书单。
新的十年,我们再启新征程。11月6日-11日,2024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在广州、深圳举办。文学与时代同行,让我们从花地出发,在湾区相遇,与世界汇流。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总执行:胡泉 陈桥生
统筹:邓琼 吴小攀
执行统筹:朱绍杰 孙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