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出版社推出鲍十全新长篇小说《我是扮演者》。该作品以日记的形式,讲述了演员孟千夫的从业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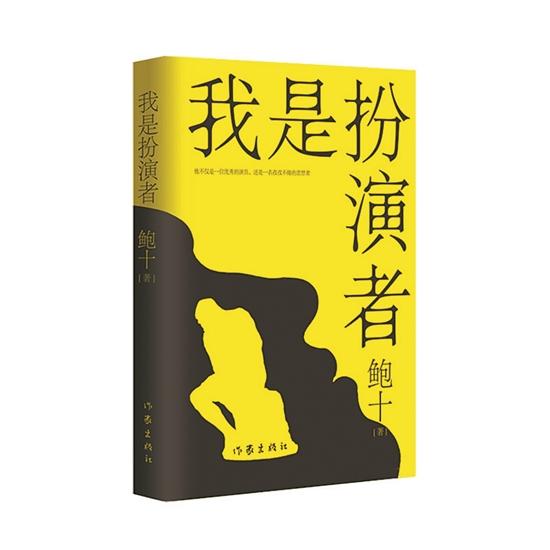
在日记中,孟千夫对自己扮演的每个角色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与思考,不论是帝王、灾民和饥民、知识分子、乡绅地主,还是士兵、下岗工人、小偷、杀人凶手、黑社会成员……把他扮演的角色串联起来,相当于一部别样的中国社会史。主人公深入且专注于自己的角色,他坚持把自己称作“扮演者”,直到生命结束。
《我是扮演者》的文本具有探索性,叙述富有张力,内容与结构均有一定的创新性,阅读时给人带来强烈的新奇感。
“写我想写的,写我能写的。不想写的东西我不会去写!”鲍十经常这样说。小说创作一直是鲍十的“业余”工作,他的主业是文学期刊编辑。三年前,他退休了,“退休后有时间了,我就想认真地写那么几部作品”。

新作选择以演员、电影来贯穿历史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择演员这样的题材、写一个似乎“入戏太深”的演员?
鲍十:用一个演员演电影这种方式来结构我的小说,跟我所要表达的主题是有关系的。
文学介入生活、介入社会的角度有很多,可以用传统的方式,比如讲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通过人物的命运来表达主题。但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东西,显然用这种传统的方式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在创作初期,我想把中国历史“兜”一下,通过对历史的扫描反思一些东西。所以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演话剧、唱歌的方式,最后采用了现在这个办法,用一个演员,他演了多部电影,把整部小说串联起来。
这个演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有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在写他的时候,不能完全按照作者的意思来左右他。他爱读书,小时候经历过一些事情,成长环境等各种因素决定他成为这样一个人:敏感、多思、有修养。作为体验派的演员他要去演,要投入,入戏很深,这也决定了他会受到外部环境、受到所扮演角色的影响和伤害。
羊城晚报:您的早期作品《纪念》曾被张艺谋执导改编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此次选择电影作为创作素材,和第一次“触电”有关系吗?
鲍十:应该说也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可能因为我接触过电影,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种形式,但没有更深的关系了。
羊城晚报:您是想通过演员的悲剧来传递什么?
鲍十:客观来说是反思他所不适应的、不能接受的东西。
实际上小说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写这个演员,一部分是通过写他所演的电影来写历史。我最初的想法是通过他来写我要写的故事,但写一个人,他必须要活起来,他必须得有自己那一套,你就得尊重他行动的逻辑。他在演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伤害,他又不接受,纠结到最后就导致他的悲剧。
羊城晚报:书中演员孟千夫说:“把我扮演过的角色串联起来,差不多就是一部五花八门的中国历史。”其实您写这本书是否有这样的野心,把中国历史的真实样貌撕开给读者看?
鲍十:不能说是野心,只是有这个意识。小说的初衷就是把历史上比较典型的事情,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让读者思考。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如果不好好反思,那是很可惜的。
“跨界”创作仍重在表达内心感受
羊城晚报:有人评论您这本小说带着先锋色彩。从写作题材上看,它跟以往相比有不同吧?
鲍十:我是农村出身的,从小在农村长大,高考之后才进了城。我对农村生活的印象非常深,这也影响到我的写作,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写乡土。后来也写了城市的生活,到了广州之后又写了一些关于广州的,这两年写了几篇关于海岛的小说。
《我是扮演者》在我的写作中是个另类,我自己给它定义为一种跨界,突然写了个演员,写了一个文艺人士,对我来说是一种跨界体验。
我说不准它是否属于先锋写作,我以前的写作基本都是按照传统的方法,通过一个故事来传达我的思考。这部长篇采用的是一种碎片化的表现方式,一部电影等于是一个碎片,可以把小说中的一个个故事当成一个个碎片,最后把碎片拼接到一起,就会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状态。我以后再写肯定还会有新的呈现方式,但是对文学的认识不会变,文学本质的情感、精神、人性的外化,这是文学真正的内核。
羊城晚报:在构思的时候做了哪些功课?
鲍十:小说框架有了之后,我查了很多资料,包括读一些历史书和回忆性的文章,读了好多。我必须找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让小说充实起来,让它真正成为一部作品。
羊城晚报:也有评论家认为您构想中的电影有“第四代”的痕迹。书中主角孟千夫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表演,恰好迎来中国电影“第四代”浪潮,在选材和写作中您参考过那个时代的群体特征吗?
鲍十:我没想过。可能读者从我小说所写的那些电影,能感觉到“第四代”导演的风格,但我不是有意要贴近“第四代”,我所想的是我要表达的东西。
羊城晚报:以前跨界编剧的经验对您现在创作这部小说也会有帮助?
鲍十:客观上肯定是有帮助。在《我的父亲母亲》之前我是没写过电影剧本的,那么有了这部作品以后,我就知道电影剧本怎么写了,起码知道了一些基本的东西。
羊城晚报:这次写“另类”的题材,您希望能达到怎样的突破?
鲍十: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个人想得最多还是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包括对文学的理解,也包括对文学的责任。
戏剧性太强也会“充满套路”
羊城晚报:距离您上一次写长篇小说已经有20年了,后来您可能更多写短篇,为什么隔了这么久又开始写长篇?
鲍十:主要的原因是没时间,退休之前我一直在做编辑,有十几年,我的创作实际上一直处于业余状态。每天一到单位有各种杂事,到家就累得不行,根本没有大块时间来写长一点的作品,只好写一些中短篇。一个短篇也得断断续续地写个十来天。所以这么多年没写长篇的原因主要是时间问题,也许这是一个借口。
羊城晚报:这一部小说您酝酿了多久?
鲍十:最早是个中篇《扮演者手记》,2014年在《花城》杂志发表。后来我慢慢把它写成长篇。因为有好多文友看了之后都说好,说它“另类”,跟当下的小说有些不同。受到这些鼓励,我就想完善它,结果就写成了长篇。从中篇到现在成稿出版,这8年多时间我也没有办法用全部精力去写。
羊城晚报:编辑的身份能为您写小说提供什么新的视角或帮助?
鲍十:我还真想谈谈这个问题。从30来岁就做编辑,一直到退休,我得看多少稿子?这种看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厌倦的过程,很多小说大概都是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些人物,充满雷同。通过阅读稿子,我对文学有了自己的判断。我后来非常厌恶那种拿腔作调,讲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很多小说都是这个德性,充斥着所谓爱恨、决裂、伤感等,大概逃不脱这些套路,思考的容量非常小。
后来,我就非常推崇那种不像小说的小说。越像小说实际上越没劲,它的情节确实非常完整,两个人相遇了,闹矛盾了,又和好了,又闹矛盾了,最后和好了,或者最后分开了;或者一个人一开始很潦倒,碰到谁就醒悟了,奋斗了,最后成功了,又失败了,戏剧性太强,充满套路。
我后来越来越不喜欢这种小说,包括自己写作时,明明可以写那种读起来很带劲的情节,但我不想那样写,就把它打散一点,让它看起来不像小说。
羊城晚报:不像小说的小说是怎样的?
鲍十:它可能更多表现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很细微的那些东西,那种真挚和真诚。太强的戏剧性可能会把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压住了,或者舍弃了。
好的小说给影视作品提供好的基础
羊城晚报:文学改编影视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之后,您在写作时会多一些考虑影视化的可能吗?
鲍十:没考虑过。包括已经拍成电影的《纪念》,正在影视化的《岛叙事》,还有卖出版权的《子洲的故事》,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都没有考虑影视化,偶然就撞到而已。导演或者编剧、策划看到了,觉得有拍成电影的可能性,就来找上门了。我的关注点还是在文学上。
羊城晚报:正在影视化的作品,您担任了编剧或者文学策划吗?
鲍十:《岛叙事》我做策划,几个人坐在一块谈剧本的改编。
羊城晚报:这跟小说创作有什么感受不一样的地方?
鲍十:策划就是大家互相碰撞,要综合大家的意见,不完全是自己的。这些不同的想法都是有益的,对我有所启发,思路更开了。
羊城晚报:那对小说创作会不会有您说的这种启发?
鲍十:写小说是另一回事,写小说你就会把那些东西放到一边了,进入的是小说的语境。电影和文学差异还是很大的。简单来说,写小说我坐在这里可以想到老家东北,可以想到南极,但是电影不行,电影要面对一个画面,做不到那么自由。
羊城晚报:您认为小说家能为编剧行业带来什么?
鲍十:真正意义上的好的小说家,其作品都是经过充分的发酵。他写一个东西,会在内心反复地酝酿,对细节非常较真,比如人物所处的环境、人物的性格,会非常认真对待。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成色肯定很好,放到影视圈里边,会给影视提供非常好的基础和方向。我个人认为一些好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是对电影的贡献。
羊城晚报:您接下来在创作或者其他方面有什么计划?
鲍十:我目前就是写几篇别人约的中短篇稿子,这期间我也在写一部长篇。现在退休后有时间了,我就想认真地写那么几部作品。

文 | 记者 陈晓楠
图 | 受访者提供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编辑 | 陈晓楠
校对 | 朱艾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