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小攀
许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长期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与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
近些年来他出版了面向公众的“解读早期中国”(《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东亚青铜潮》)、“考古纪事本末”(《发现与推理》《三星堆之惑》)等系列考古著作,尤其是关于早期中国的研究,引起广泛关注。
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十三邀》主创许知远和他做了一次有关考古的对话——

文学青年如何变成“铁杆考古人”?
许知远:你最初看到那些器物的时候,会有新奇感吗?
许宏:说起来最初不是冲着考古专业来的,当年我是想成为文学青年。
许知远:你应该是1980年上的大学吧?17岁的许宏想成为什么样的文学青年?
许宏: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几大文学杂志都看。张贤亮、刘心武之类的作家作品,读了大量的闲书。现在真的已经舍不得花时间来读什么虚构作品了,即便是有点时间,也更愿意阅读非虚构的传记。
现在看来文学还是属于青年。中学的时候跟几个同学还搞过一个文学小组,真是有作家梦。
我当年考试还考得挺好,所以有点狂妄,报志愿的时候,好多老师希望我能报得务实一点,我的第一志愿居然报了北大中文系,人大、复旦、南开、吉大让我从第二志愿到第五志愿都报上了。
非第一志愿人家当然不要,招生的时候只有山东大学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想要你,能不能去?当时管招生的老师说,你要来我们就给你安排进考古专业,考古专业很抢手。后来我进去之后才知道,山东大学历史系招生20个人,报考古专业的竟然有七八十人。
许知远:后来为什么还是选考古?
许宏:毕业实习是在山西侯马,太好的一个地方,冥冥中跟我今后的专攻密切相关。毕业实习是个分水岭,有的同学是彻底干伤了,有的就成为铁杆考古人,我就是属于后者。
刚开始怀有的是文学梦,被分到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我也问过老师能不能改行,当时是不成的。
许知远: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勉强的、意外的考古学家。
许宏:许多考古学家都是这样的。邹衡先生以前是学法律的,我的导师徐苹芳教授其实是学新闻的。当时我的考虑就是既然学不了别的,只能按照这个方向走,是金子总会闪光的,所以就逼着自己学,逼着自己钻。
到了1983年的侯马实习,我就已经成为一个铁杆考古人了,好多同学巴不得实习少点,但是我回校报考研究生后,又跟一个老师坐火车回到了侯马,在冰天雪地的时候,又接了一个探方,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就那么干下来了。

考古学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许知远:20世纪80年代初的考古学是一个什么状况?
许宏:那个时候正好是一个节点,可以把中国考古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过两年就有国外的东西进来了,而前30年的考古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探索,是孤立的,和国外学界基本脱节。
80年代,伴随整个社会的躁动和活力,我们把传统考古学、新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这些东西囫囵吞枣地努力吸收。
现在看来,不管我对这些东西懂与不懂,我觉得都给了我极大的给养,有助于我以前和现在的发展。
许知远:说说你去侯马的感觉吧。那里变成分水岭了,有人逃离考古了,有人坚定地留下来了。你去了发掘现场之后,是什么让你更坚定地做这件事情?
许宏:不喜欢考古的人要问他们自己不喜欢的原因,多种多样。喜欢的人是为什么?对我个人来说,首先是发现之美,这种对未知的好奇心。
考古学不是让你一看就看到头的学科,而是从上而下地寻觅,总会有惊喜。大家对考古感兴趣,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人类的好奇心吗?
再一个就是思辨之美。我们一直自诩,别人也这样说,考古学是文科中的理工科。有人开玩笑说文学“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历史学“有一分材料说五分话”,考古学“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但考古学家还必须有想象力,否则你就是一个无味的学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想去求证,想象力不丰富肯定不行。
许知远:你什么时候清晰地意识到考古学需要很强的想象力?
许宏:我意识到这点还是比较晚的。考古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是经验型学科,更多的是推论和假说,这些是验证不了的。
我们能证明什么?能证明的是凭着经验得出的判断,这种判断实证起来问题不大,但也有误判的时候。
考古学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比如那个圜底罐是做什么用的?我们说是煮水的、熬粥的,可以根据内壁的残留物分析出来,但大量的东西是实证不出来的,它们都是属于推论和假说层面的。
想象力应该是必需的吧,有一些推论和假说通过科技手段就落实了,有一些永远都是个秘密。我觉得这恰恰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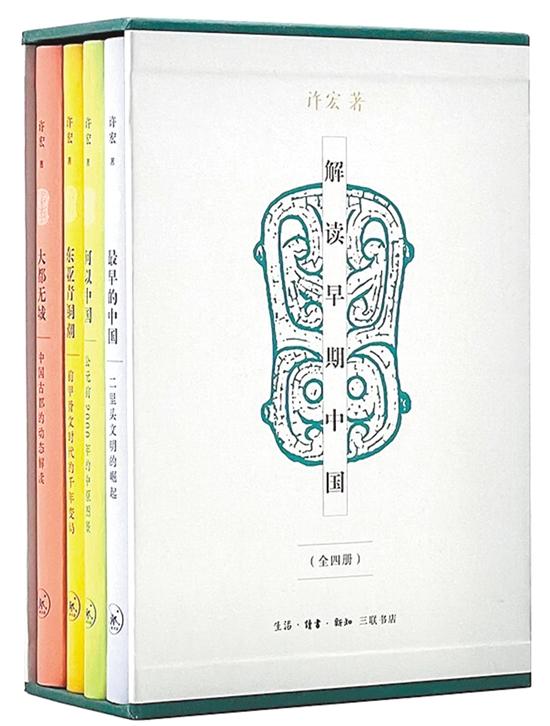
最早的中国在哪里?
许知远:1996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的时候?
许宏:对,就在那个时候。包括偃师商城的发掘,都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偃师商城时我负责1000多平方米的发掘面积,手下有两个技师、一二十个民工,现在等于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接手二里头的时候我36岁,发现最早的宫城那一年正闹“非典”,我40岁。
许知远:会有一天再做更深的挖掘,能显示、描述出二里头人的日常生活吗?
许宏:能。如果只是文献的话,那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样的东西,即便进入文献非常丰富的历史时期,好多古人日常的生产、生活细节也没有被写出来。考古学成果一出来,大大丰富了对民间性内容的认知,类似于人类学。
比如说二里头,现在我们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发掘宫殿区,但是我们也开始发掘平民的生活区了。《最早的中国》里面已经谈到,二里头人喜食烧烤,各种猪的和牛的骨头有被烧过的痕迹,这都是我们发掘出来的。
许知远:就是一群二里头人晚上坐在这儿撸串,是吗?
许宏:是这样的。比如说煮菜、蒸菜应该都有了,像蒸锅似的东西我们叫甗,但是炒菜还没有呢。还有骨针、骨簪,骨簪是当时男人、女人用来束头发的。在我们的这个大报告里面,这些东西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许知远:二里头突然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
许宏:这个就太有意思了。据文献记载,是商把夏灭了,按理说灭国那应该是一片狼藉,捣毁宫殿、墓葬什么的,但是现在据考古发现,二里头没有因战乱或暴力原因而被废弃,反而感觉像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二里头铸铜作坊一结束,郑州商城那边一个新的作坊就起来了,这种时间上的对应性,让人觉得它有一点战略转移的性质。
可能商人一开始是土包子,像这种宫室建筑,这些动产、不动产,这些礼制,几乎全盘继承了二里头,可能就像是孔子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在中国古代史上,一个落后的文化、落后的族群占领中原,成为主人之后,在文化上被中原文化同化,这种事多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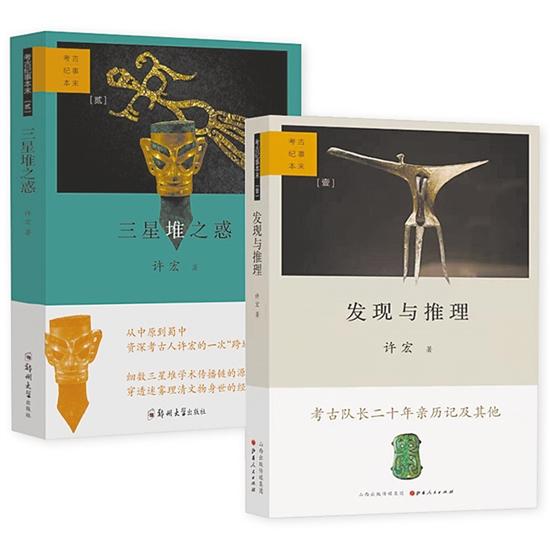
怎么判定一个器物的价值?
许知远:我问一个庸俗的问题,怎么判定这些器物值多少钱呢?
许宏:你看我们背后的器物架,从来没有类似的器物在潘家园市场出现过,这些东西按理说不怕偷,盗墓的只盗值钱的。说实话我真的不懂鉴宝,我只见过真的,没见过假的;只知道历史价值,不知道市场价值。潘家园市场大门冲哪儿开,我真的不知道。
隔行如隔山,真是这样。这种事说起来有意思,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让家长填表,一看是考古学家,说有一个朋友收藏古董,能不能给看看?
我说我真的不懂。硬着头皮去见了一面,人家就说,你怎么骑自行车来的?你挖掘的时候揣走两件,一套房子不就有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的人吗?他很敬佩我,当然也可能是鄙夷。
在考古学界,监守自盗的事非常少,人活得纯净。考古界的老先生就是这样,从李济先生他们开始就自己不收藏文物,这是整个考古界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许知远:你的使命感是什么?
许宏:使命感是有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现在处于一种更为超脱的玩学问的心态,不是说我是为了启蒙教化一代新人,真的就是已经脱离了那种爬坡阶段,不是为了稿费、为了职称、为了什么位置,这样可以让我以更加从容的心态来做学问。
所以我希望自己考虑的是,什么是最值得追求的,什么是最值得珍重的。我现在特别想走郑也夫、李零先生他们那样的路,不以个人名义申请任何项目课题,不受过多的限制和束缚。
据说美国做过这样的采访,问那些老年人,最愿意回到人生的哪个阶段。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回到50岁前后,人生已经脱离了爬坡阶段,但身体还没有衰弱到不能自理。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态,我正在享受我的人生。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编辑 | 孙旭歌
校对 | 黎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