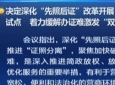《孩子梦》剧照
由以色列剧作家汉诺赫·列文编剧、伊泰·德荣导演、北马其顿共和国比托拉国家剧院演出的话剧《孩子梦》,不久前在第21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和第3届北京老舍戏剧节先后上演。演出前的高度期待和演出后的激烈争议,使这部戏剧成为近期一个引人瞩目的话题。如何理解汉诺赫·列文的这部剧作?如何看待此剧的导演呈现?此剧虽已演完,依然值得驻足探讨。
汉诺赫·列文总是触到人的痛处——似乎善良即是罪恶。他的戏剧世界里有无尽的拷问,将罪恶放大后进行诗意的推波助澜,他也宁可抛出各种隐藏真相的象征。他的人物都在一条走向死亡的旅途中,他没有原谅苦难深重之中的作恶,从《孩子梦》到《安魂曲》皆是如此,当复杂的人性里散发出阴暗,罪恶与赎罪成了列文戏剧里的一大特征。
列文非常尖锐的政治性都是和庸常的人生联系在一起的。《孩子梦》里的指挥官、船长、移民官和岛长,看上去是权力的符号,但他们是和身边那些普通人共同构成了罪孽。如果说列文的戏剧是一艘驶向未知的船,那茫茫大海之中一定有死亡宿命的笼罩,以及短暂而难得的纯净童话世界的苏醒,他们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列文纠缠于病魔之中的脆弱,如《安魂曲》里的天使,又如《孩子梦》里的亡童,这只是黑暗中的一道亮光。
所以,当以色列“90后”导演伊泰·德荣在舞台上安排了蜡烛,在水面上漂浮时,我完全被感动了。我非常赞同马其顿版《孩子梦》这样的处理,宛如塔可夫斯基电影《乡愁》中那段手捧蜡烛的精神漫游的再现,这符合汉诺赫·列文的风格——用美丽而素白的意象来祈祷。
真正要了解汉诺赫·列文,可能要对他的背景做一些探究。他的父母是波兰犹太人,比他大9岁的长兄大卫·列文出生在波兰,二战爆发之后全家才漂泊到特拉维夫。尽管列文出生在以色列,但他有着波兰人坚硬而负重的一面。在汉诺赫·列文走向戏剧与诗歌的道路上,离不开他的长兄大卫的影响——他早期的戏剧是由在卡梅尔剧院担任导演的大卫搬上舞台的。关于希伯来语的创作,我们也许更应该追溯二战之后那几代以色列的作家群。著名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和那单·扎赫都是从德国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这两位和列文有着深刻渊源关系的诗人,以及杰出的小说家大卫·格罗斯曼都曾活跃在戏剧界。耶胡达·阿米亥和那单·扎赫同属于“解放一代”,遵循自由的创作道路而抛弃上一代作家的集体意识,这和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以色列现实状况有关。
《孩子梦》里很多台词,几乎就是一首首带有普世意义的诗歌——尽管我们尚且不能直接读到列文作为诗人的那一面,也无从了解耶胡达·阿米亥对他有多少引领作用。但如果拿阿米亥的诗歌和列文的剧本作对照,就会发现共同的痛苦的母题,以及宗教观上的归属。“人们在明亮得痛苦的大厅里/谈论现代人/生活中的宗教/以及上帝在其中的位置。”(耶胡达·阿米亥《大宁静:问与答》),这可以用来解读列文,只是列文将其放置在救生艇或者马车上。
《孩子梦》是宗教诘问方面特别突出的一出杰作,加上年轻一代以色列戏剧导演在舞美与影像上的处理,舞台上呈现了海洋和岸的关系,也就是死亡和拯救的关系。那艘无望的救生艇和几件穿在乘客身上的橙色的救生衣,很符合列文对于死亡思考的画面感。特别想说的是,列文写《孩子梦》是基于那部同样在中国很有影响力的英国电影《苦海余生》的启发——这是一个基于历史事实的故事:纳粹将数百名犹太人赶上一艘无人敢接纳的“死亡之船”,以此给犹太人刻上污名。
列文伟大的文本在舞台上的呈现总有着后人的加工成分。比如马其顿版的《孩子梦》里用老者来扮演熟睡中的孩子,包括借鉴电影《苦海余生》里的真人秀“Love Boat”的场景,还有邀请观众上台担任乘客的环节。尽管这第二幕开头的一场不免让人有点出戏,但事实上这恰恰是列文本人也无比注重的一点——观众的进入感。列文沉痛而又令人捉摸不透的台词,也许是一种心灵的抚慰,但更有力的是他尖锐的政治观,他想给剧场里所有的人重重的一拳,让人意识到罪恶与生俱来,暴力只是行动的结果。“时代变了,道别来得太奢侈”,当这句话出现时,列文的当代性也被巧妙地实现。
《孩子梦》是列文早期向后期过渡时期的作品,也就是既有批判的深刻性,又有潜意识里的深刻表达。当现实的残忍和人性的恶毒,共同到达死亡的彼岸时,“我的童年,一去不返”的诗意是赤裸裸地展现的。这是列文特征最为混杂的一部杰作。所有的象征充满血腥,所有的无望又是“上帝死了”的回声。最后一幕《弥赛亚》渗透着欧洲电影大师如伯格曼晚年的宗教情绪:亡童们围成一个圆圈躺着,直至经过了漫长逃生的孩子也加入进来,使这一幕好像是野外的弥撒仪式,悲悼大于控诉。列文关于死亡的思考充满了想象力,这也是他独一无二的体验。当医生宣布了丧钟将要提前响起的时刻,列文的艺术终极地平线多了一道深深的影子。
我有幸在《孩子梦》的上海场被随机挑选,作为乘客坐上救生艇,近距离地观看了第二幕和第三幕。舞台上的水营造了黑洞一样的沉陷感,当船长在水边对着母亲发泄他的兽欲时,你能隐约听到来自深渊的求救。一米以内目睹扮演母亲的女演员脸颊上的泪水,它仿佛是一个放大的现实和噩梦交错的视角,令我不寒而栗。
这一版的《孩子梦》使用的是马其顿语,导演的视觉语言和肢体语言的成熟度超出了他的年龄。比如原著中弥赛亚贩卖手表的细节带有列文讽刺的宗教意识,但伊泰·德荣没有渲染夸张的意味,而将隐喻包裹在救赎的交响中。当然,我们更想得到希伯来语境里悲痛的信息,那应该是更浑厚的诗意,显然导演的处理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略显抽象的苍白。
列文把孩子的梦,转换成“格尔尼卡”式的悲悼。逝去的究竟是什么?死亡永远被生命这头的进行式所触碰。我清晰地记得,站在耶路撒冷的哭墙边,听到飘荡在空中的《安魂曲》的那一刻,所感觉到的人类之渺小。这和汉诺赫·列文的文字深处,应该是一致的。(孙孟晋)

80571eac-c1f7-44e3-a707-ac2f0050eac2.jpg)

476606e0-7c0a-4ca4-bcaf-c47ae267337a474de806-1a50-473a-8a20-e9e1dafd7043.jpg)
ca265386-3601-487f-96fc-100f4e33c6cb.jpg)




7441bd35-d965-490e-a37d-d8daec195dd7.jpg)
3ffeb52d-15db-4c9e-ba8e-4eb6a3a1a204.jpg)
75c9b2d6-be57-4662-b16f-562c15a456d4.jpg)
d6f1c253-7141-4592-87fd-598309afda41.jpg)

3721220e-09ac-4287-aaa4-b7c16303ac7d.jpg)
7eaa3db6-f4df-4f54-bd59-67eb054657b5.jpg)
5a546e94-f197-43d1-8c66-5ce0a3a30b8a.jpg)